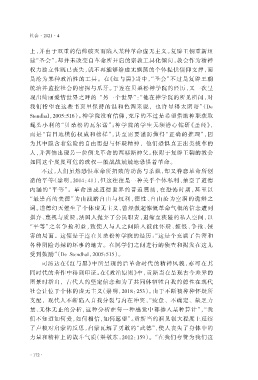Page 179 - 《社会》2021年第4期
P. 179
社会·2021·4
上,并由于双重的信仰破灭而陷入某种革命虚无主义。 复辟王朝重新组
建“圣会”,却并未改变自革命所开启的宗教工具化倾向,教会作为精神
权力独立性既已丧失,就不再能够给虚无飘荡的个体提供信仰支撑,而
是沦为某种政治性的工具。 在《红与黑》当中,“圣会”不过是复辟王朝
统治并监控社会的密探与爪牙。 于连在贝桑松神学院的经历,又一次呈
现出绮丽爱情世界之畔的“另一个世界”:“他在神学院的所见所闻,对
我们指望在这些书页里保持的温和色调来说, 也许显得太阴暗”( De
Stendhal,2005:516)。 神学院没有信仰,充斥的不过是希望借助神职获取
蝇头小利的“贝桑松的瓦尔诺”;神学院的学生无须潜心钻研《圣经》,
而是“盲目地模仿权威和榜样”,甚至需要谨防懂得“正确的推理”,因
为其中隐含着危险的自由思想与怀疑精神, 他们恐惧真正出类拔萃的
人,并害怕出现另一位倒戈革命的西耶斯神父。 依附于复辟王朝的教会
如同这个岌岌可危的政权一般战战兢兢地恐惧着革命。
不过,人们虽然恐惧革命所招致的动荡与杀戮,却又眷恋革命所创
造的平等(崇明,2014:41),但这往往是一种关乎个体私利、抽空了道德
内涵的“平等”。 革命造成道德世界的普遍震荡,在恐怖时期,甚至以
“最崇高的美德”为由践踏自由与权利,德性、自由沦为空洞的诡辩之
词。 道德幻灭催生了个体虚无主义,曾经激起慷慨革命气概的信念遭到
摒弃、蔑视与质疑,法国人抛弃了公民职责,退缩至狭隘的私人空间,以
“平等”之名争抢利益,致使人与人之间陷入彼此怀疑、嫉恨、争抢、侵
害的局面。 这便是于连在贝桑松神学院的经历:“这是个充满了告密和
各种阴险毒辣的坏事的地方。 在同学们之间进行的侦查和揭发在这儿
受到鼓励”(De Stendhal,2005:515)。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所呈现的后革命时代的精神风貌,亦可在其
同时代的著作中得到印证。在《政治原则》中,贡斯当在呈现古今差异的
图景时指出, 古代人的坚定信念和为了共同体牺牲自我的德性在现代
社会让位于个体的虚无主义(崇明,2018:253)。 由于不断被种种怀疑所
支配, 现代人不断陷入自我分裂与内在冲突,“疲惫、 不确定、 缺乏力
量、无休无止的分析,这种分析在每一种感觉中都掺入某种算计”,“我
们不知道如何爱,如何相信,如何愿望”。贡斯当的洞见很大程度上延续
了卢梭对启蒙的反思,启蒙瓦解了勇敢的“武德”,使人丧失了身体中的
力量和精神上的战斗气质(渠敬东,2012:159)。“在我们夸赞为我们这
· 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