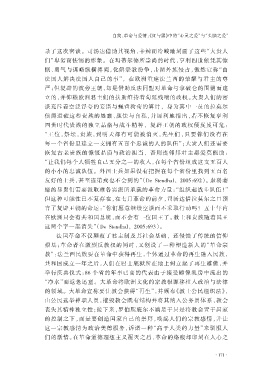Page 178 - 《社会》2021年第4期
P. 178
自我、革命与爱情:《红与黑》中的“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
录了这次密谈。 司汤达借助其视角,辛辣而冷峻地刻画了这些“大贵人
们”卑劣而怯懦的形象。 在玛蒂尔德所崇尚的时代,亨利四世依凭其慷
慨、勇气与谋略纵横捭阖,化解宗教纷争,击溃外族侵占,傲然宣称“由
法国人解决法国人自己的事”, 在欧洲重建法兰西的荣耀与君主的尊
严;但复辟的波旁王朝,却是借助反法同盟对革命与拿破仑的围剿而建
立的,并仰赖欧洲君主们的扶助维持着苟延残喘的政权。 大贵人们的密
谈充斥着空泛浮夸的妄语与蝇营狗苟的算计, 身为其中一员的拉莫尔
侯爵道破这些贵族的愚蠢、胆怯与自私,并犀利地指出,若不恢复亨利
四世时代贵族的独立品格与战斗精神, 复辟王朝的政权便岌岌可危:
“王位,祭坛,贵族,到明天都有可能被消灭,先生们,只要你们没有在
每一个省份里建立一支拥有五百个忠诚的人的队伍”;大贵人们还需要
恢复古老贵族的慷慨品质与政治担当, 否则连邻邦君主都爱莫能助:
“让我们每个人牺牲自己五分之一的收入,在每个省份组成这支五百人
的小小的忠诚队伍。 外国士兵如果没有把握在每个省份里找到五百名
友好的士兵,甚至连第戎也不会到的”(De Stendhal, 2005:692)。 虚弱萎
靡的显贵们需要汲取雅各宾派所承载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战斗队伍!”
但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在七月革命的前夕,司汤达借拉莫尔之口预
言了复辟王朝的命运:“你们愿意继续空谈而不采取行动吗? 五十年内
在欧洲只会有共和国总统,而不会有一位国王了。 教士和贵族随着国王
这两个字一起消失”(De Stendhal, 2005:693)。
法国革命不仅颠覆了君主制及其社会基础, 还侵蚀了传统的信仰
根基;革命者在激烈反教权的同时,又创设了一种塑造新人的“革命宗
教”:法兰西民族要在革命中获得再生,个体通过革命的再生融入民族,
共和国成立一年之后,人们在巴士底狱所在地上树立起了再生雕像,并
举行庆典仪式:86 个省的年事已高的代表由于接受雕像乳房中流出的
“净水”而返老还童。 大革命将欧洲文化的宗教根源移植入政治与法律
的领域。 大革命宣称要让教会获得“再生”,并颁布《教士公民组织法》,
由公民选举神职人员,摧毁教会既有结构并将其纳入公务员体系,教会
丧失其精神独立性;接下来,罗伯斯庇尔不满足于只是将教会置于国家
的控制之下,而是要创造国家自己的崇拜,唤起人们的宗教感情,并让
这一宗教感情为政治美德服务,诉诸一种“高于人类的力量”来驯服人
们的激情。 在革命道德理想主义覆灭之后,革命的烙痕却印刻在人心之
·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