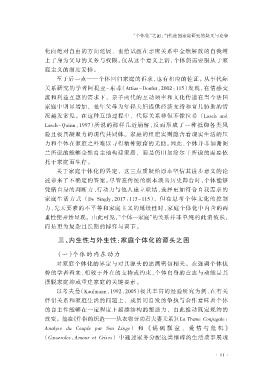Page 18 - 《社会》2021年第2期
P. 18
“个体化”之困:当代法国家庭研究的疑义与论争
化向绝对自由的方向延展, 也给试图在亲密关系中全然解放的自我缚
上了身为父母的义务与权限。 仅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仍需要服从于家
庭主义的制度安排。
至于后一点——个体回归家庭的诉求,也有相应的佐证。 从事代际
—
关系研究的学者阿提亚-东菲(Attias-Donfut,2002:115)发现,在情感交
流和利益互惠的需求下, 亲子两代的互动频率和文化传递在当今法国
家庭中明显增加, 老年父母为年轻夫妇提供经济支持和育儿协助的情
况越发常见。 在这种互助过程中, 代际关系非但不像拉希 (Lasch and
Lasch-Quinn,1997)所说的那样几近崩解,反而形成了一种抵御各类风
险且极具凝聚力的现代共同体。 家庭的组建实则隐含着现实生活的压
力和个体在家庭之外难以寻得精神慰藉的无助。 因此,个体并非如谢阁
兰所说的能够全然自主地构建家庭, 而是仍旧如涂尔干所说的需要依
托于家庭而生存。
关于家庭个体化的界定, 这三点质疑给原本坚信其进步意义的论
述带来了不确定的答案。 尽管在传统的剧本淡出历史舞台时,个体能够
凭借自身的判断力、行动力与他人建立联结,选择更加符合自我需求的
家庭生活方式 (De Singly,2017:113-115), 但在思考个体文化的控制
力、先天要素的不平等和家庭主义的延续性时,家庭个体化中内含的两
重性便开始显现。 由此可见,“个体—家庭”的关系并非单纯的此消彼长,
而是更为复杂且长期的博弈与调节。
三、内生性与外生性:家庭个体化的源头之困
(一)个体的内在动力
对家庭个体化的界定与对其源头的追溯密切相关。 在强调个体优
势的学者看来,相较于外在的支持或约束,个体自身的意志与动能是其
摆脱家庭抑或重建家庭的关键要素。
以考夫曼(Kaufmann,1992,2005)极其丰富的经验研究为例,在有关
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的问题上, 成员间自发的争执与合作意味着个体
的自主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结构的塑造力, 由此推动既定规约的
改变。 他在《伴侣的织造———从衣物劳动看夫妻关系》(La Trame Conjugale:
Analyse du Couple par Son Linge) 和 《锅 碗 瓢 盆 、 爱 情 与 危 机 》
(Casseroles,Amour et Crises) 中通过家务分配这类细碎的生活琐事展现
·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