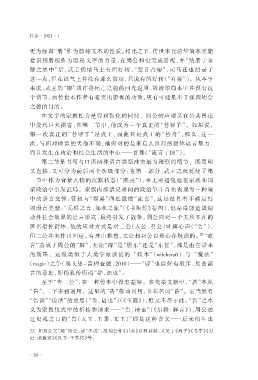Page 27 - 《社会》2021年第1期
P. 27
社会·2021·1
更为强调“册”作为隐秘文本的性质。相比之下,传世本比清华简本更能
意识到册祝作为隐秘文字的力量,在周公和史完成册祝,并“纳册于金
縢 之匮中”后,武王病情马上有所好转,“翌日乃瘳”,司马迁也照录了
这一点,但在语气上并没有那么肯定,只说有所好转(“有瘳”)。 从本事
来说,武王的“瘳”或许是死亡之前的回光返照,故清华简本中并没有这
个情节。 而传世本作者有意突出册祝的功效,更有可能是出于强调周公
之德的目的。
在文字的宗教性力量得到强化的同时, 周公的声望又在公共舆论
中受到巨大损害,在第二节中,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替罪羊”。 如果说,
第 一 次 真 正 的“替 罪羊 ”是 武 王 ,而 他 只 是 武 王 的“替 身 ”,那 么 ,这 一
次,与面对靡常的天命不同,他面对的是来自人世间的群体语言暴力,
而且发生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首都(“流言于国”)。
第二节是书写与口语两种语言类型冲突最为剧烈的情节, 既简明
又直接,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次级部分:在第一部分,武王之死延续了第
一节中作为背景人物的沉默状态(“既丧”),并无可避免地在家族和国
家政治中引发乱局。 家族内部诸兄弟间的政治争斗首先表现为一种暗
中的语言交锋:管叔与“群弟”四处撒播“流言”,这是最具有不确定性
的语言类型:“无根之言,如水之流”(《书集传》卷四),也是最能造成煽
动性社会效果的语言形式,最终引发了战争。 周公面对一个无所不在的
匿名指控群体,他的应对方式是对二公(太公、召公)吐露心声(“告”),
22"
但二公并未作出回应。 有理由推想,太公和召公也是心存疑虑的。 “流
言”造成了周公的“辟”,无论“辟”是“居东”还是“东征”,都是由它带来
的效果, 这很类似于人类学家谈论的“妖 术 ”(witchcraft) 与“魔 法 ”
( magic)之争(埃文思-普理查德,2010)———“辟”也恰好有驳斥、反击谣
言的意思,即伪孔传所谓“辟,法也”。
至于“告二公”,在三种传本中没有差异。 在先秦文献中,“诰”本从
“告”,二字多相通用。 这里的“告”作动词用,并非名词“诰”。 它当然有
“告诉”“说话”的意思(“告,语也”)(《玉篇》),但又不尽于此。“告”之本
义为宗教仪式中的祈祷和请求———“告,请也”(《尔雅·释言》),周公通
过史祝之口的“告(太王、王季、文王)”即是这种含义———后来 衍生 出
22. 如召公之“疑”周公,或“不说”,故周公作《君 奭》以释其疑,又见于《列子》《书序》《史
记·燕世家》《汉书·王莽传》等。
·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