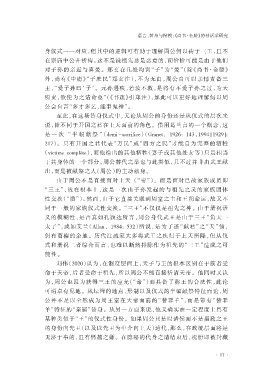Page 24 - 《社会》2021年第1期
P. 24
语言、替身与楷模:《尚书·金縢》的神话学研究
身仪式一一对应,但其中的逻辑可有助于理解周公何以祷于三王,且不
在宗庙中公开祈祷。 这不是说祖先总是恶意的,而恰恰可能是由于他们
对子孙的亲近与喜爱。 郑玄在几处均训“子”为“爱”(除《尚书·金 縢》
外,尚有《中庸》“子庶民”郑玄注),不为无由,周公自可以亲情责备三
王,“爱子孙曰‘子’。 元孙遇疾,若汝不救,是将有不爱子孙之过,为天
所责,欲使为之请命也”(《书疏》引郑注),如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何以周
公会自言“多才多艺,能事鬼神”。
至此,在这场替身仪式中,无论从周公的身份还是从仪式的层次来
说,皆不同于开国之君在上天面前的角色。 借用葛兰言的一个概念,这
是 一 次 “半 幅 献 祭 ”( demi -sacrifice)(Granet, 1926: 143,1994 [1929]:
217)。 只有开国之君代表“万民”或“四方之民”才能自为完整的牺牲
( victime complète),而他给出的其他牺牲(妻子或其他处女等)只是相当
于其身体的一个部分。 周公替代之举也与此类似,只不过并非由武王献
出,而是被献祭之人(周公)的主动献身。
由于周公不是直接面对上天 (“帝”), 而是面对已故家族成员即
“三王”,故在根本上,这是一次由子孙发起的与祖先之灵的家族团体
性交换(“质”)。 然而,由于它直接关联到周室之主和王朝命运,故又不
同于一般的家族仪式性交换。“三王”不仅仅是祖先之神。 由于册祝语
义的模糊性,是否真如孔颖达所言,周公身代武王是由于三王“负天一
太子”,或如艾兰(Allan, 1984: 532)所说,是为了还“弑君”之“天”债,
仍有商榷的余地。 历代注疏家大多将武王之疾归于上天所降,但从仪
式和册祝二者综合而言,也难以断然排除作为祖先的“三王”造成之可
能性。
刘伟(2020)认为,在制度层面上,天子与王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受
命于天帝,后者受命于祖先,所以周公不能直接祈请天帝。 他同时又认
为,周公也因为获得三王的应允(“命”)而具备了称王的合法性,此论
可谓卓有见地。 从坛墠的地点、形制以及仪式的半幅献祭特征而论,周
公并不足以全然成为周王室在天帝面前的“替罪羊”,而是带有“替罪
羊”特征的“亲属”替身。 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某种类似于“王”的仪式性身份。 如果周公只是以诸侯而不是摄政之王
的身份向先王(以及以先王为中介向上天)请代,那么,在政统层面将是
无济于事的,且有僭越之嫌。 在隐秘的代身之请结束后,祝册即被封藏
·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