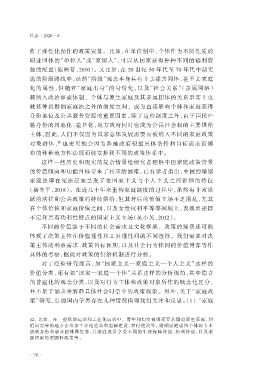Page 85 - 《社会》2020年第6期
P. 85
社会·2020·6
作了弹性化操作的政策安排。 比如,在单位制中,个体作为不同性质的
职业团体的“单位人”或“家属人”,可以从国家获得种种不同的福利资
源的配置(陈映芳,2010)。 又比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实
施的阶级路线中,虽然“阶级”观念本身具有非亲缘共同体,甚至去家庭
化的属性,但随着“家庭出身”的身份化,以及“社会关系”(亲属网络)
被纳入政治审查体制, 个体与原生家庭及其亲属团体的关系事实上也
被延伸到婚姻家庭法之外的制度空间, 成为直接影响个体和家庭获得
身份地位及公共服务资源的重要因素。 除了这些制度之外,由于国民户
籍身份的属地化、差异化,地方政府同时也成为公民社会权的主要供给
主体,因此,人们不仅因为国家总体发展需要而被纳入不同的家庭政策
12
对象群体, 也更可能会因为各地政府根据具体条件和目标需求而颁
布的种种地方性法规而被安排到不同的政策体系中。
这样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情景给研究者理解中国家庭政策背景
的价值倾向和功能目标带来了相应的困难。 已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婚姻
家庭法律在宪法层面呈现了在国家 主义 与 个人 主 义 之 间 徘 徊 的特 征
(唐冬平,2018)。 在近几十年来重构家庭制度的过程中,虽然有非常活
跃的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持续供给,但其背后的价值立场不乏混乱,尤其
在个体价值和家庭价值之间,以及女性权利平等等问题上,表现出摇摆
不定和具有功利性特点的国家主义立场(吴小英,2012)。
不同的价值源于不同的社会需求及文化框架, 政策的摇摆还可能
体现了决策主体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间的不同选择。 我们需要对决
策主体的利益需求、政策目标预期,以及社会行为体间的价值博弈等作
具体的考察,据此对政策的供给机制进行分析。
对于经验研究而言,如“国家主义—家庭主义—个人主义”这样的
价值分类,还有如“国家—家庭—个体”关系这样的分析视角,其中隐含
的普遍化的观念分类,以及对行为主体和政策对象所作的概念化区分,
并不足于涵盖并解释具体社会时空中的政策现象。 另外,关于“家庭政
策”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存在几种情况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1)“家庭
12. 比如, 在一些政治运动和工业化运动中, 青年和妇女被国家要求脱离原生家庭,到
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参加工业化运动和边疆建设、农村建设等。 婚姻家庭也因个体的专业
级别身份和职业团体属性等,其家庭成 员享受不同的生活保障待遇、福利待遇,以及家
庭团聚的照顾性政策等。
·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