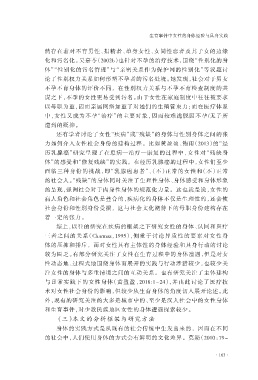Page 170 - 《社会》2020年第6期
P. 170
生育事件中女性的身体经验与具身实践
然存在着对不育男性、捐精者、单身女性、女同性恋者及其子女的边缘
化和污名化。 吴嘉苓(2002b)也针对不孕的治疗技术,围绕“性别化的身
体”“性别化的污名管理”与“亲密关系作为保护网的性别化”等议题讨
论了性别权力关系如何形塑不孕者的污名处境。 她发现,社会对于男女
不孕不育身体的评价不同, 在性别权力关系与不孕不育检查制度的共
谋之下,不孕的女性更易受到污名。 由于女性在家庭制度中往往被要求
以母职为重,因而亲属网络加重了对她们的生殖管束力;而在医疗体系
中,女性又成为不孕“治疗”的主要对象,因而较难逃脱因不孕/无子所
遭到的贬抑。
还有学者讨论了女性“疾病”或“残缺”的身体与性别身体之间的张
力如何介入女性社会身份的建构过程。 比如黄盈盈、鲍雨( 2013)的“经
历乳腺癌”研究呈现了在患病—治疗—康复的过程中,女性对“残缺身
体”的感受和“修复残缺”的实践。 在经历乳腺癌的过程中,女性们至少
面临三种身份的挑战,即“乳腺癌患者”、(不)正常的女性和(不)正常
的社会人。“残缺”的身体同时关注了生理性身体、身体感受和身体形象
的呈现,强调社会对于肉身性身体的规范化力量。 这也就是说,女性的
病人角色和社会角色是叠合的,疾病化的身体不仅是生理性的,还会使
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受损, 这与社会文化期待下的母职身份建构存在
着一定的张力。
综上,以往的研究在疾病的框架之下研究女性的身体、认同和医疗
三者之间的关系( Charmaz,1995),侧重于讨论异 质 性的 要 素 对女性身
体的压抑和排斥, 而对女性具有主体性的身体经验和具身行动的讨论
较为匮乏。 有部分研究关注了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身体遭遇,但是对女
性动态地、过程式地围绕身体而展开的实践与行动涉猎较少,也较少关
注女性的身体与多重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也有研究关注了主体建构
与日常实践下的女性身体(黄盈盈,2018:1-24),并由此讨论了医疗技
术对女性社会身份的影响,但较少从生育身体的角度切入展开论述。 此
外,现有的研究关注的大多是城市中的、至少是汉人社会中的女性身体
和生育事件,对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身体遭遇探索较少。
(三)本文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身体的实践方式是从既有的社会传统中生发出来的, 因而在不同
的社会中,人们使用身体的方式会有鲜明的文化差异。 莫斯(2010:79-
· 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