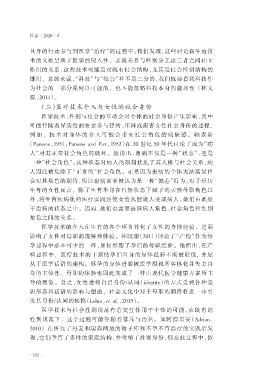Page 169 - 《社会》2020年第6期
P. 169
社会·2020·6
具身的行动参与到医学“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讨论新生殖技
术的文献呈现了医学的侵入性、 亲属关系与性别分工这三者之间相互
作用的关系,这些技术可能是对既有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性别结构的
挪用。 总的来说,“科技”与“社会”并不是二分的,我们既要看到科技作
为社会的一部分是何以可能的, 也不能忽略科技本身的能动性 (林文
源,2014)。
(二)医疗技术介入与女性的社会身份
医学技术、性别与社会的互动会对个体的社会身份产生影响,其中
可能伴随着异质性的要素参与建构、压抑或损害女性社会身份的过程,
例 如 , 技 术 对 身 体 的 介 入 可 能 会 带 来 社 会 角 色 的 残 缺 感 。 帕 森 斯
( Parsons,1951;Parsons and Fox,1952)在 20 世纪 50 年代讨论了成为“病
人”对其正常社会角色的破坏。 他指出,患病不仅是一种“状态”,还是
一种“社会角色”。这种状态对病人的限制扰乱了其人格与社会关系,病
人因此被免除了“正常的”社会角色。 正是因为患病的个体无法满足社
会对其角色的期待,所以患病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偏差”行为。对于经历
生育的女性而言, 除了生育本身在自然状态下赋予的天然母职角色以
外,将生育疾病化的医疗实践还使女性从健康人变成病人。 她们由此处
于患病的状态之中。 因而,她们也需要协调病人角色、社会角色和性别
角色之间的关系。
医学技术的介入在生育的各个环节异化了女性的身体经验, 进而
影响了女性对母职的理解和体验。 林晓珊( 2011)讨论了“产检”作为怀
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如何形塑了孕妇的母职经验。 他指出,在产
检过程中, 医疗技术的干预使孕妇自身的身体经验不断被贬低, 并屈
从于医学话语的建构。 怀孕的身体进而被医学凝视所客体化并失去自
身的主体性, 母职的体验也因此变成了一种由现代医学健康方案所主
导的想象。 总之,女性建构自己身份/认同(identity)的方式受到各种意
识形态和话语的影响与塑造, 社会文化中对于母职的期待将进一步引
发其身份/认同的转换(Lehto,et al.,2019)。
医学技术与社会性别规范有着交互作用于个体的可能,在既有的
性别规范下, 这个过程可能伴随着排斥与污名。 如阿德里安(Adrian,
2010) 在研究了丹麦和瑞典两地的精子库和不孕不育治疗的实践后发
现,它们孕育了多样的家庭结构,并重塑了性别身份,但在此过程中,依
· 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