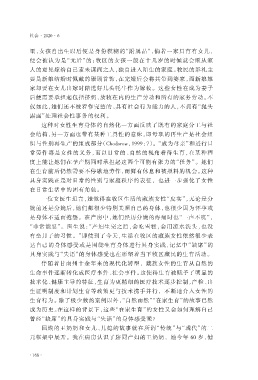Page 175 - 《社会》2020年第6期
P. 175
社会·2020·6
里,女孩自出生以后便是身份模糊的“附属品”,倘若一家只育有女儿,
便会被认为是“无后”的;牧区的女孩一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会顺从家
人的意见嫁给自己素未谋面之人,独自进入陌生的家庭。 牧民的彩礼主
要是新娘结婚时佩戴的珊瑚首饰,在完婚后会将其带到婆家,而新娘娘
家却要在女儿出嫁时陪送好几头牦牛作为嫁妆。 这些女性在成为妻子
后便需要承担起包括挤奶、放牧在内的生产劳动和所有的家务劳动。 不
仅如此,她们还不被看作完整的、具有社会行为能力的人,不拥有“抛头
露面”处理社会性事务的权利。
这种对女性生育身体的自然化一方面反映了既有的家庭分工与社
会结构,另一方面也带有某种工具性的意味,即母职的再生产是社会组
织与性别再生产的组成部分( Chodorow,1999:7)。“成为母亲”和进行日
常劳作都是女性的义务,而以日常的、自然的视角看待生育,在某种程
度上能让她们在孕产期同时承担起这两个可能有张力的“任务”。 她们
在生育前后仍然 7 需要不停歇地劳作,而鲜有休息和被照料的机会。 这种
具身实践正是对日常的性别与家庭秩序的表征, 也进一步强化了女性
在日常生活中的固有角色。
一位女医生坦言,她觉得在牧区生活的藏族女性“ 皮实”,无论是分
娩前还是分娩后,她们都很少特别关照自己的身体,也很少因为怀孕或
是身体不适而抱怨。 在产房中,她们经历分娩的疼痛时也“一声不吭”,
“非常能忍”。 医生说:“产妇生完之后,会吃雪糕,会用凉水洗头,也没
有坐月子的习惯。 ”即使到了今天,生活在牧区的藏族女性依然很少表
达自己的身体感受或是围绕生育身体进行具身实践,记忆中“缺席”的
具身实践与“失语”的身体感受也在形塑着当下牧区藏民的生育活动。
伴随着甘南州十余年来的现代化转型, 藏族女性的生育从自然的
生命事件逐渐转化成医疗事件、社会事件。 这使得生育被赋予了明显的
技术化、健康主导的特征,生育为更精细的医疗技术逐步控制,产检、出
10. 这
生证明制度和计划生育等政策更与技术携手并行, 不断地介入女性的
生育行为。 除了极少数的案例以外,“自然而然”“在家生育”的故事已然
成为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在家生育”的女性又会如何理解自己
曾经“缺席”的具身实践与“失语”的身体感受呢?
回族的王奶奶和女儿、儿媳的故事就在所谓“传统”与“现代”的二
元框架中展开。 我在病房认识了陪同产妇的王奶奶, 她今年 60 岁,健
· 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