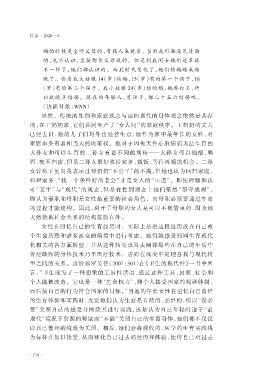Page 177 - 《社会》2020年第6期
P. 177
社会·2020·6
婚的时候是全听父母的,有媒人来说亲。 当时我们都没见过面
的,也不认识,直接都凭父母说的。 但是到我闺女她们这辈就
不一样了,她们都认识的。 而且时代变化了,她们结婚越来越
晚了。 你看我大姑娘 14(岁)结婚,15(岁)有的第一个孩子,16
(岁)有的第二个孩子。 我小姑娘 24(岁)结的婚,她要打工,所
以就晚点结婚。 现在的年轻人,男孩子,都二十五六结婚吧。
(访谈对象:WNN)
显然, 传统的性别和家庭观念与面向现代的身体观念依然是共存
的,在王奶奶家,它们共同生产了“女人间”的家庭秩序。 王奶奶的丈夫
已经去世,她的儿子们均外出经营生意,她作为家中最年长的女性,对
家庭事务有着相当大的决策权。 她对于因先天性心脏病而无法生育的
大孙女和可以生育的二孙女有着不同的期待——大孙女可以抽烟、喝
—
酒、夜不归宿,但是二孙女最好收拾家务、做饭、等待再婚的机会。 二孙
女曾私下里向我表示过对奶奶“不公平”的不满,但她也认为回归家庭、
料理家务、“找一个条件好的老公”才是女人的“正道”。 即使理解和认
可“卫生”与“现代”的观念,但是在性别观念上她们依然“墨守成规”,
即认为妻职和母职是女性最重要的社会角色, 而母职必须要通过生育
的过程才能建构。 因此,离开了母职的女人是可以不被管束的,因为她
天然就被社会关系的结构排除在外。
女性在回忆自己的生育经历时, 实际上是把这段经历放在自己整
个生命历程和诸多流变的情境中进行考虑。 她们能感受到同生育现代
化相关的各方面转型, 并从这种转变出发去阐释那些在自己的生活中
曾经缺席的身体技术乃至医疗技术, 进而在流变中处理自我与现代转
型之间的关系。 这恰如罗芙芸(2007:301)在《卫生的现代性》一书中所
言:“卫生成为了一种想象的工具性话语,通过这种工具,国家、社会和
个人能被改造。 它也是一种‘生命权力’,即个人接受国家的规训体制,
而后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国家的目标。 ”当地的年长女性在追忆自己曾经
的生育体验和实践时,无论她们认为生育是自然的、必经的,所以“没必
要”关照自己的感受并围绕其进行实践,还是认为自己年轻时迫于“前
现代”境况下资源的稀缺而“不能”关照自己的生育身体,她们都不仅仅
以自己曾经的境遇为关照。 相反,她们会将现代的、医学的生育实践视
为标杆并加以接受,从而矮化自己过去的经历和体验,使得自己对过去
· 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