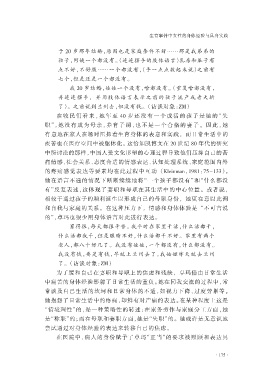Page 182 - 《社会》2020年第6期
P. 182
生育事件中女性的身体经验与具身实践
于 20 岁那年结婚,原因也是家庭条件不好……那是我弟弟的
孩子,阿姨一个都没有。(连连摆手的肢体语言)乳房和肚子有
点不好,不舒服……一个都没有,(手一点点数起来说)之前有
七个,但是还是一个都没有。
我 20 岁结婚,娃娃一个没有,啥都没有。(重复啥都没有,
并连连摆手, 并用肢体语言表示之前的孩子流产或者夭折
了)。 之前说到兰州去,但没有钱。 (访谈对象:ZM)
在 牧 民 们 看 来 , 她 年 至 40 岁 还 没 有 一 个 成 活 的 孩 子 是 她 的“失
职 ”,她 没 有 成 为 母亲 ,养 育子 嗣 ,也 不 是 一 个 合 格 的 妻 子 。 因 此 ,她
有意地在家人在场时压抑着生育身体的表意和实践, 而日常生活中的
疾苦也在医疗空间中被躯体化。 这恰如凯博文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
中所讨论的那样,中国人受文化形塑的心理过程导致他们压抑自己的苦
痛情感,社会关系、态度合适的情感表达、认知处理系统、家庭范围内外
的疼痛感觉表达等要素均在此过程中互动 (Kleinman,1981:75-133)。
她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地将“一个孩子都没有”和“什么都没
有”反复表述,这体现了妻职和母职在其生活中的中心位置。 或者说,
相较于通过孩子的顺利诞生以形成自己的母职身份, 她更在意以此调
和自我与家庭的关系。 在这种压力下, 情感和身体体验是“不可言说
的”,卓玛也很少用身体语言对此进行表达。
累得很,每天都很辛苦。 我平时在家里干活,什么活都干,
什么活都我干,但是眼睛不好,什么活都干不好。 家里有两个
老人,都八十好几了。 我没有娃娃,一个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钱,要是有钱,早就上兰州去了,我妯娌昨天就去兰州
了。 (访谈对象:ZM)
为了缓和自己在妻职和母职上的焦虑和残缺, 卓玛借由日常生活
中痛苦的身体经验影射了日常生活的重负。 她在同我交流的过程中,常
常谈及自己生活的坎坷和日常身体的不适,如视力下降、过度劳累等。
她抱怨了日常生活中的疼痛,却鲜有对产痛的表达。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
“情境理性”的,是一种策略性的转述:在家务劳作与家庭分工方面,她
是“ 称职”的;而在母职和妻职方面,她是“失职”的。 她或许是无意识地
尝试通过对身体经验的表达来转移自己的焦虑。
在医院中,病人的身份赋予了卓玛“正当”的要求被照顾和表达具
· 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