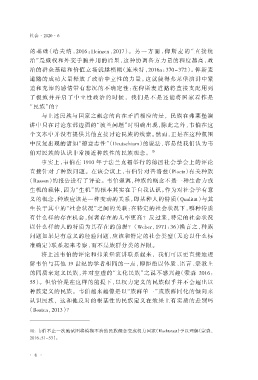Page 15 - 《社会》2020年第6期
P. 15
社会·2020·6
的 基 础(哈 夫 纳 ,2016;Heinzen,2017)。 另 一 方 面 , 俾 斯 麦 的“直 接 统
治”是威权和外交手腕并用的后果,这种协调各方力量的程度越高,政
治的群众基础和价值立场就越模糊(施米特,2016a:370-372)。 俾斯麦
道路的成功大量释放了政治中立性的力量。 这就使得弗莱堡演讲中紧
迫和充沛的感情带有悲沉的不确定性:在俾斯麦道路将直接支配用到
了极致并开启了中立性政治的时 候 , 我 们是 不 是 还 能 将 国 家 看 作 是
“民族”的?
与上述民族与国家之概念的内在矛盾相应的是, 民族在弗莱堡演
讲中只在讨论东部边疆的“波兰问题”时明确出现,除此之外,韦伯在这
个文本中并没有提供其他直接讨论民族的线索。 然而,正是在这种氛围
中反复出现的诸如“德意志性”( Deutschtum)的说法,容易使我们认为韦
伯对民族的认识非常接近种族性的民族观念。 10
事实上,韦伯在 1910 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社会学会上的评论
直接针对了种族问题。 在该会议上,韦伯针对普洛兹( Ploetz)有关种族
(Rassen)的报告进行了评论。 韦伯强调,种族的概念不是一种生命力或
生机的载体,因为“生机”的根本其实在于自我认识。作为对社会学有意
义的概念,种族应该是一种变动的关系,即某种人的特质( Qualit覿t)与其
生长于其中的“社会状况”之间的关联:在特定的社会状况下,哪种特质
有什么样的存在机会,何者存在的几率更高? 反过来,特定的社会状况
以什么样的人的特质为其存在的前提? (Weber,1971:36)换言之,种族
问题如果是有意义的经验问题,应该和特定的社会类型(无论以什么标
准确定)联系起来考察,而不是族群分类的界限。
将上述韦伯的评论和弗莱堡演讲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更直接地理
解韦伯与其他 19 世纪的学者相同的一点,即拒绝以体质、语言、宗教上
的同质来定义民族,并对空虚的“文化民族”之说不感兴趣(蒙森 2016:
55)。 但恰恰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以权力定义的民族似乎并不会超出以
种族定义的民族。 韦伯越来越像是以“族群单一”或族群同化的倾向来
认识民族, 这和他反对的根基性的民族定义在效果上有实质的差别吗
(Boatca,2013)?
10. 韦伯不止一次地试图将模糊不清的民族概念变成权力国家(Machtstaat)予以理解(蒙森,
2016:51-53)。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