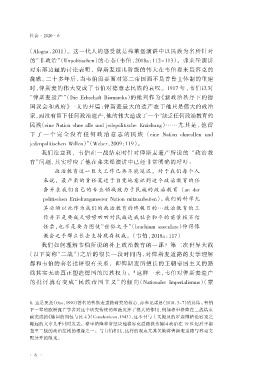Page 13 - 《社会》2020年第6期
P. 13
社会·2020·6
(Alagna,2011)。 这一代人的感受就是弗莱堡演讲中以民族为名所针对
的“非政治”(Unpolitischen)的心态(韦伯,2018a:112-113)。 弗莱堡演讲
对东部边疆的讨论表明, 俾斯麦超出阶级的伟大在韦伯看来是容克的
挽歌。 二十多年后,当韦伯需要面对第二帝国而不是普鲁士体制的重建
时,俾斯麦的伟大变成了韦伯对德意志民族的哀叹。 1917 年,韦伯以对
“俾斯麦遗产”(Die Erbschaft Bismarcks)的批判作为《新政治秩序下的德
国议会和政府》一文的开篇:俾斯麦最大的遗产在于他只是伟大的政治
家,而没有留下任何政治遗产,他的伟大造成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
民族( eine Nation ohne alle und jedepolitische Erziehung)…… 尤 其 是 , 他 留
下 了 一 个 完 全 没 有 任 何 政 治 意 志 的 民 族 (eine Nation ohneallen und
jedenpolitischen Willen)”(Weber,2009:119)。
我们注意到, 韦伯在一战结束时针对俾斯麦遗产所说的“政治教
育”问题,其实呼应了他在弗莱堡演讲中已经非常明确的呼吁:
政治教育这一巨大工作已再不能延迟。 对于我们每个人
来说, 最严肃的责任莫过于自觉地意识到这个政治教育的任
务并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致力于民族的政治教育 ( an der
politischen Erziehungunserer Nation mitzuarbeiten)。 我们的科学尤
其必须以此作为我们的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政治教育的工
作并不是要成天唠唠叨叨对民族达成社会和平的前景投不信
任票,也不是要力图使“世俗之手”( brachium saeculare)伸得像
教会之手那么长去支持现存权威。 (韦伯,2018a:117)
我们如何理解韦伯所说的补上政治教育的一课?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下简称“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俾斯麦道路的史学理解
都和韦伯的著名批评很有关系, 即俾斯麦所擅长的王朝帝国主义的路
线其实无法真正塑造德国的民族权力。 8 这样一来,韦伯对俾斯麦遗产
的 批 评 就 有 变 成“民 族 帝 国 主 义 ”的 倾 向( Nationaler Imperialismus)(蒙
8. 这是奥托(Otto,1990)著名的俾斯麦道路研究的核心,亦参见诺恩(2018:3-7)的总结。 韦伯
下一辈的欧洲流亡学者对这个研究传统的塑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格申格隆在二战结束
前完成的《德国的面包与民主》(Gerschenkron,1943),这本书与上文提及的罗森博格论容克之
崛起的文章几乎同时发表。 格申格隆非常坚决地将容克道路视为德国政治在 19 世纪后半期
直至二战的政治悲剧的根源之一。 与韦伯相比,这样的观点尤其欠缺将俾斯麦道路与容克支
配分开的眼光。
·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