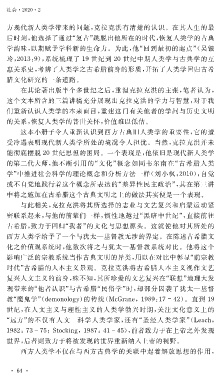Page 71 - 《社会》2020年第2期
P. 71
社会 · 2020 · 2
方现代新人类学带来的问题 , 克拉克洪有清楚的认识 。 在其人生的最
后时刻 , 他选择了通过 “ 复古 ” 跳脱出他所在的时代 , 恢复人类学的古典
学韵味 , 以期赋予学科新的生命力 。 为此 , 他 “ 回到最初的起点 ”( 吴银
玲 , 2013 : 9 ), 系统梳理了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中期人类学与古典学的互
惠关系史 , 考辨了人类学之古希腊前身的形质 , 开拓了人类学回归古希
腊文化研究的一条道路 。
在其论著出版半个多世纪之后 , 重温克拉克洪的主张 , 笔者认为 ,
这个文本所含的三篇讲稿充分展现出克拉克洪的学力与智慧 , 对于我
们重新认识人类学的本来面目 , 重建这门有关他者的学问与历史文明
的关系 , 恢复人类学的普世关怀 , 价值难以低估 。
这本小册子令人重新认识到西方古典旧人类学的重要性 , 它的遭
受冷遇表明现代新人类学所处的境况令人担忧 。 当然 , 克拉克洪并未
能彻底摆脱 20 世纪思想的困局 。 一个表现是 , 他依旧是现代新人类学
的第二代大师 , 他不断引用的 “ 文化 ” 概念如同韦尔南在 “ 古希腊人类
学 ” 中推进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一样 ( 刘小枫 , 2010 ), 自觉
或不自觉地践行着这个概念所表达的 “ 差异性民主政治 ”, 其在第三讲
中将之施加在古希腊这个古典文明之上的做法其实便是一个表现 。
与此相关 , 克拉克洪将其所选择的志业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紧
密联系起来 , 与他的前辈们一样 , 惯性地越过 “ 黑暗中世纪 ”, 直接前往
古希腊 , 致力于回归 “ 我者 ” 的文化与思想源头 。 这就使他对其所处的
西方人类学给予了一个与犹太 — 基督教无涉的界定 。 在陈述古希腊文
化之价值观系统时 , 他数次将之与犹太 — 基督教系统对比 。 他将这个
影响广泛的宗教系统当作古典文明的异类 , 用以在对比中彰显 “ 前宗教
时代 ” 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景观 。 克拉克洪将古希腊人本主义视作文艺
复兴人文主义的前身 , 殊不知 , 其所珍爱的文艺复兴在 “ 联想 ” 地理大发
现带来的 “ 他者认识 ” 与古希腊 “ 民俗学 ” 时 , 却部分因袭了犹太 — 基督
) 的传统 ( 犕犮犌狉犪狀犲 , 1989 : 17-42 )。 直到 19
教 “ 魔鬼学 ”( 犱犲犿狅狀狅犾狅 犵狔
世纪 , 在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人类学勃兴时期 , 关注文化意义上的
“ 远方 ” 的不仅有人文 — 科学人类学家 , 还有 “ 圣经人类学家 ”( 犔犲犪犮犺 ,
1982 : 73-75 ; 犛狋狅犮犽犻狀 犵 1987 : 41-45 ), 前者致力于在上帝之外发现
,
世界 , 后者则致力于将被发现的世界重新纳入上帝的视野 。
西方人类学不仅在与西方古典学的关联中起着解放思想的作用 ,
· 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