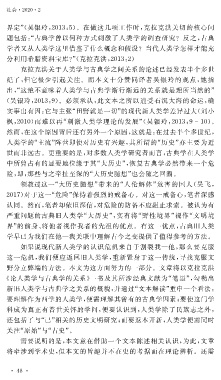Page 55 - 《社会》2020年第2期
P. 55
社会 · 2020 · 2
界定 ”( 吴银玲 , 2013 : 5 )。 在做这几项工作时 , 克拉克洪关切的核心问
题包括 :“ 古典学曾以何种方式刺激了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反之 , 古典
学者又从人类学这里借鉴了什么概念和假设?当代人类学怎样才能充
分利用希腊资料宝库? ”( 克拉克洪 , 2013 : 2 )
克拉克洪关于人类学与古典学之间关系的论述已经发表半个多世
纪了 , 但它极少引起关注 。 而本文十分赞同译者吴银玲的观点 , 她指
出 ,“ 这绝不意味着人类学与古典学渐行渐远的关系就是理所当然的 ”
( 吴银玲 , 2013 : 9 )。 必须承认 , 此文本之所以遭受石沉大海的命运 , 确
实事出有因 : 它与主张 “ 田野就是一切 ” 的现代新人类学差异过大 ( 刘小
枫 , 2010 ) 而难以再 “ 刺激人类学理论的发展 ”( 吴银玲 , 2013 : 9-10 )。
然而 , 在这个原因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 这就是 :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 ,
人类学的 “ 主流 ” 阵营即使对历史有兴趣 , 其所谓的 “ 历史 ” 亦主要为近
世而非远古 。 更重要的是 , 对多数人类学研究者而言 , 古典学在人类学
中所曾占有的显要地位缘于其 “ 大历史 ”, 恢复古典学必然带来一个危
险 , 即 , 那些与之牵扯至深的 “ 大历史臆想 ” 也会随之回潮 。
领教过这一 “ 大历史臆想 ” 带来的 “ 人伦解体 ” 危害的国人 ( 吴飞 ,
2017 ) 对于这一 “ 危险 ” 保持着强烈的戒备心 。 对这一戒备心 , 笔者深感
认同 。 然而 , 笔者却依旧深信 , 对危险的防备不应阻止求索 。 被认为有
严重问题的古典旧人类学 “ 大历史 ”, 实有将 “ 野性境界 ” 视作 “ 文明境
界 ” 的前身 、 将他者视作我者的先祖的优点 。 有这一优点 , 古典旧人类
学早已为我们在他 — 我关联中理解古今之变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方法 。
如果说现代新人类学的认识危机来自于割裂我 — 他 , 那么要克服
这一危机 , 我们便应返回旧人类学 , 重新置身于这一传统 , 寻找克服文
野分立弊端的方法 。 本文为这方面努力的一部分 。 文章将以克拉克洪
《 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 》 一书及其所涉经典文献为 “ 笔墨 ”, 勾勒出
新旧人类学与古典学之关系的概貌 , 并通过 “ 文本解读 ” 重申一个看法 :
要理解作为西学的人类学 , 便需理解其曾有的古典学因素 ; 要使这门学
科成为真正有普世关怀的学问 , 便要认识到 , 人类学除了民族志之外 ,
还包括了与 “ 己 ” 相关的历史文明研究 ; 而要返本开新 , 人类学便需同时
关注 “ 原始 ” 与 “ 古史 ”。
需要说明的是 , 本文意在借助一个文本陈述相关认识 , 为此 , 文章
将牵涉到学术史 , 但本文的旨趣并不在史的考据而在理论辨析 。 还需
·
4
·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