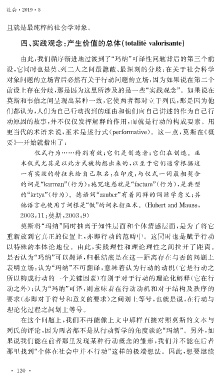Page 127 - 《社会》2019年第5期
P. 127
社会· 2019 · 5
且就是最纯粹的社会学对象。
四、实践观念:产生价值的总体( 狋狅狋犪犾犻狋é狏犪犾狅狉犻狊犪狀狋犲 )
由此,我们循序渐进地过渡到了“玛纳”可译性问题背后的第三个前
设,它同时也是莫、列二人之间最隐蔽、最深刻的分歧:在关于社会科学
对象问题的立场背后必然有关于行动问题的立场,因为如果说在第二个
前设上存在分歧,那是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些“实践观念”。如果说在
莫斯和韦伯之间呈现出某种一致,它使两者都对立于列氏,那是因为他
们都认为,人们为自己行动找到的理由和他们向自己讲述的作为自己行
动原因的故事,并不仅仅发挥解释的作用,而就是行动的构成要素。用
更当代的术语来说,巫术是述行式( 犲狉犳狅狉犿犪狋犻狏犲 )。这一点,莫斯在《概
狆
要》一开始就指出了:
仪式行为……特别有效;它们是创造者;它们在创造。巫
术仪式尤其是以此方式被构想出来的,以至于它们通常根据这
一有实效的特征来给自己取名:在印度,与仪式一词最相契合
的词是“ 犽犪狉犿犪狀 ”(行为);施咒迷惑就是“ 犳犪犮狋狌犿 ”(行为),是典型
的“ 犽狉狋 狔 犪 ”(行为)。德语词“ 狕犪狌犫犲狉 ”有着同样的词源学意义;其
他语言也使用了词根是“做”的词来指巫术。( 犎狌犫犲狉狋犪狀犱犕犪狌狊狊 ,
2003 : 11 ;莫斯, 2003 : 9 )
莫斯将“玛纳”同时抽离于知性层面和个体情感层面,是为了将它
重新放到它真正的位置上,亦即行动的范畴中。这同时也是赋予行动
以特殊的本体论地位。由此,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之间拉开了距离。
是否认为“玛纳”可以翻译,归根结底是在这一距离存在与否的问题上
表明立场:认为“玛纳”不可翻译,意味着认为行动的动机(它是行动之
所以构成行动的一个关键因素)有别于对于行动的理论化解释(它在行
动之外);认为“玛纳”可译,则意味着在行动动机和对于结构及秩序的
要求(亦即对于符号和意义的要求)之间划上等号,也就是说,在行动与
理论化过程之间划上等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再能像上文中那样直接对照莫斯的文本与
列氏的评论,因为两者都不是从行动哲学的角度谈论“玛纳”。另外,如
果说我们能在前者那里发现某种行动概念的雏形,我们并不能在后者
那里找到“个体在社会中并不行动”这样的极端想法。因此,想要继续
· 1 2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