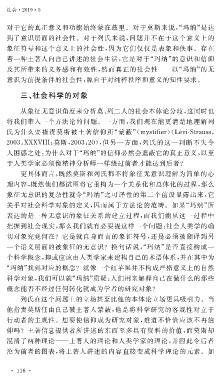Page 123 - 《社会》2019年第5期
P. 123
社会· 2019 · 5
对于它的真正意义和功能始终蒙在鼓里。对于莫斯来说,“玛纳”是达
到了意识层面的社会性。对于列氏来说,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意义上的
象征符号和这个意义上的社会性,因为它们仅仅是表象和佚事。存在
着一种土著人向自己讲述的社会生活,它是对于“玛纳”的意识和信仰
及其所带来的义务感和有效性,然而真正的社会性———以“玛纳”的无
意识为前提条件的社会性,源自于对纯粹秩序和意义的知性要求。
三、社会科学的对象
从象征无意识角度来分析莫、列二人的社会本体论分歧,这同时也
将我们带入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现在能更清楚地理解列
氏为什么要指责莫斯被土著信仰所“蒙蔽”( 犿 狔 狊狋犻犳犻犲狉 )( 犔é狏犻犛狋狉犪狌狊狊 ,
2003 : 犡犡犡犞犐犐犐 ;莫斯, 2003 : 20 ),但另一方面,列氏的这一判断不失令
人困惑之处:为什么对于“玛纳”的信仰必然会遮蔽它的真正意义,以至
于人类学家必须像精神分析师一样绕过前者才能达到后者?
更具体而言,既然莫斯和列氏都不将象征无意识理解为简单的心
理内容,既然他们都试图将它重构为一个关系化和总体化的过程,那么
象征无意识的复杂性就令“玛纳”之可译性的第二个前设显露出来,它
关乎对社会科学对象的定义,因而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如果“玛纳”所
表达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象征关系的建立过程,而我们能从这一过程中
把握到社会现实,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提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人类学的确
切对象究竟何在?它是就自身而言的象征符号,还是必须被翻译到另
一个语义层面的被象征的无意识?换句话说,“玛纳”是否直接构成一
个科学概念,抑或应该由人类学家来建构自己的术语体系,并在其中为
“玛纳”找到对应的概念?就像一个红苹果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自然
科学对象,我们可以就“玛纳”质疑:人们用来解释自己在做什么的那些
概念能否不经过任何转化就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
列氏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甚至比他的本体论立场更具吸引力。当
他指责莫斯任由自己被土著人蒙蔽,他是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对立于
行动者的主观性。想要使信仰成为研究对象,难道不恰恰应该不再信
仰吗?土著信息提供者所讲述的东西至多具有资料的价值,而莫斯却
混淆了两种理论———土著人的理论和人类学家的理论,并因此令后者
沦为前者的图表,将土著人讲述的内容直接变成科学理论的元素。如
· 1 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