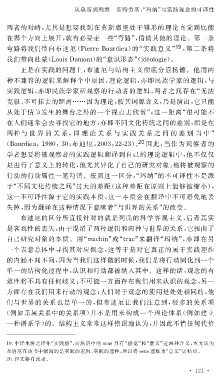Page 128 - 《社会》2019年第5期
P. 128
从莫斯到列维—斯特劳斯:“玛纳”与实践观念的可译性
两者的对峙,尤其是想要找到在莫斯那里处于雏形的理论直觉到底能
在哪个方向上展开,就有必要走一些“弯路”,借助其他的理论。第一条
弯路将我们带向布迪厄( 犘犻犲狉狉犲犅狅狌狉犱犻犲狌 )的“实践意义” 19 ,第二条将
我们带向杜蒙( 犔狅狌犻狊犇狌犿狅狀狋 )的“意识形态”( 犻犱é狅犾狅 犵 犻犲 )。
正是在实践的问题上,布迪厄与结构主义彻底分道扬镳。他用两
种不兼容的逻辑来解释个中原因:理论逻辑,亦即民族学家的逻辑,与
实践逻辑,亦即民族学家所观察的行动者的逻辑,两者之间存在“无法
克服、不可抹去的距离……因为理论,按其词源含义,乃是演出,它只能
从处于情节发生的舞台之外的一个视点去欣赏”;这一距离“很可能不
在人们通常会去寻找它的地方,亦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而是在
两种 与 世 界 的 关 系,即 理 论 关 系 与 实 践 关 系 之 间 的 差 别 当 中 ”
( 犅狅狌狉犱犻犲狌 , 1980 : 30 ;布迪厄, 2003 : 2223 )。 20 因此,当作为观察者的
学者想要将被观察者的实践逻辑翻译到自己的理论逻辑中,他不仅仅
是进行了意义上的转化,他尤其异化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他将被观察的
行动的行动属性一笔勾销。按照这一区分,“玛纳”的不可译性不是源
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过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在原则上能够被缩小),
这一不可译性源于它的实践本质,这一本质会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丢
失掉,因为翻译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与世界的关系”的改变。
布迪厄的区分所直接针对的就是列氏的科学客观主义,后者其实
是客观性的丧失:由于混淆了两种逻辑和两种与世界的关系,它扭曲了
自己研究对象的本质。用“ 犿犪犮犺犻狀 ”或“ 狋狉狌犮 ”来翻译“玛纳”,亦即在另
一个表意总体中寻找其对应概念,这等于是对它真正的属于实践理性
的内涵不闻不问,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将行动同化到一个
单一的结构化过程中,认识和行动都被纳入其中。这样的话,观念的有
效性将不具有任何歧义:不可能一方面存在我们用来认识的观念,另一
方面存在我们用来行动的观念;人们对于观念的使用是处处相同的,他
们与世界的关系也是单一的,但布迪厄让我们注意到,很多的关系项
(例如亲属关系中的关系项)并不是用来构成一个理论体系(例如建立
一种谱系学)的。结构主义常常这样错误地认为,并因此不惜任何代价
19. 中译本将之译作“实践感”,而法语中的 狊犲狀狊 具有“感觉”和“意义”这两种含义,本文认为
布迪厄在该书中强调的是实践的逻辑、实践的理性,所以将 狊犲狀狊理解为“意义”更贴切。
20. 译文略有改动。
· 1 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