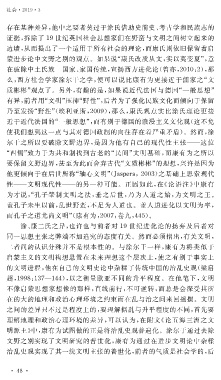Page 55 - 201903
P. 55
社会· 2019 · 3
存在某种差异,他中之要者莫过于涂氏借助史前史、考古学和民族志的
证据,拆除了 19 世纪英国社会思想家们在野蛮与文明之间树立起来的
边墙,从而提出了一个适用于所有社会的理论,而康氏则依旧保留着启
蒙进步论中文野之别的观点。如果说“康氏改质从文,实以夷变夏”,意
在破除中土氏族—国家、家国传统,宣扬西方进化论(曾亦, 2010 : 2 ),那
么,西方社会学家涂尔干之学,便可以说比康有为更接近于儒家之“文
质彬彬”观点了。另外,有趣的是,如果说近代法国与德国“一般思想”
有异,前者用“文明”压抑“野性”,后者为了强化民族文化而倾向于保留
乃至发扬“野性”(埃利亚斯, 2009 ),那么,康氏观点实比涂氏理论更接
近于近代法国的“一般思想”,而有别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化观(这不免
使我们想到这一点与其对德国政制的向往存在着严重矛盾)。然而,涂
尔干之所以要破除文野边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现代性主张———这位
“西儒”致力于为共和制找到古老的“民间”文明基础,而康有为之所以
要保留文野边界,甚至为此而舍弃古代“文质彬彬”的理想,兴许是因为
他更倾向于在后世所称“轴心文明”( 犑犪狊 狆 犲狉狊 , 2003 )之基础上思索现代
性———文明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能。正因如此,在《论语注》中康有
为才说,“孔子肇制文明之法,垂之后世,乃为人道之始,为文明之王。
盖孔子未生以前,乱世野蛮,不足为人道也。盖人道进化以文明为率,
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康有为, 2007 :卷九, 445 )。
涂、康二氏之异,也许也与前者对 19 世纪进化论的扬弃及后者对
同一思想主张之弊端不加追究的态度有关。然而必须指出,有关文明,
二者间的认识分殊并不是根本性的。与涂尔干一样,康有为将类似于
启蒙主义的文明构想悬置在未来理想这个层次上,使之有别于事实上
的文明进程,他在自己的文明史论中杂糅了传统中国的治乱史观(梁启
超, 1998 : 137 — 144 ),以之衡量欧亚不同的升平程度。在他笔下,文明
不像启蒙思想家想像的那样,直线前行,不可逆转,而总是会深受其所
在的大的地理和政治心理环境之约束而在乱与治之间来回摇摆。文明
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程度上的,要理解据乱与升平程度的不同,首先要
理解地理和政治心理环境的差异,可以认为,在附文《论五海三洲之文
明源土》中,康有为试图做的正是将治乱史观普遍化。涂尔干通过去除
文野之别实现了文明研究的普世化,康有为通过在进步文明论中杂糅
治乱史观实现了其一统文明主张的普世化,前者的气质是社会学的,后
· 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