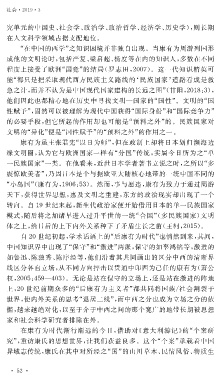Page 59 - 201903
P. 59
社会· 2019 · 3
究单元的中国史、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则长期
在人文科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
“在中国的西学”之知识困境并非独自出现。当康有为周游列国形
成他的文明论时,包括严复、梁启超、杨度等在内的知识人,多数在不同
程度上接受了欧洲“国竞”的结局(罗志田, 2007 )。这一代知识精英可
能“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国家’道路看成是救
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甘阳, 2018 : 3 ),
他们因此也都精心地在历史中寻找文明—国家的“国性”。文明的“国
性赋予”,固然可以被理解为现代中国获得“国际身份”和“国际竞争力”
的必要手段,但它所起的作用却也可能是“预料之外”的。民族国家对
文明的“异化”便是“国性赋予”的“预料之外”的作用之一。
康有为虽主张君宪“以日为师”,但在政制上却将日本划归濒海边
缘文明圈,认为它与欧洲国家一样有“分国”传统,实属今日所为之“单
一民族国家”一类。在他看来,近世日本学者著书立说之时,之所以“多
震惊欧美者”,乃因日本是个与据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一统中国不同的
“小岛国”(康有为, 1906 : 53 )。然而,事与愿违,康有为致力于通过周游
天下,获得世界思想,惠及文明之重建,东方的政治现实却出现了一个
转向。自 19 世纪末起,新生代政治家便开始借用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
模式,随后将之加诸早进入过升平世的一统“合国”(多民族国家)文明
体之上,给日后的上下内外关系种下了矛盾生长之苗(王柯, 2015 )。
自 20 世纪初起,学术话语上的“后康有为时代”也悄然到来,其间,
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保守”和“激进”两派,保守的如辜鸿铭等,激进的
如鲁迅、陈独秀、陈序经等,他们沿着其共同画出的区分中西的清晰界
线区分各自立场,从不同方向抨击以贯通中印西为己任的康有为(萧公
权, 2005 : 459 — 403 )。无论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激进的阵地
上, 20 世纪前期众多的“后康有为主义者”都共同将国族/社会割裂于
世界,使内外关系的思考“退居二线”,而中西之分也成为立场之分的依
据,越来越绝对化,以至于介于中西之间的那个宽广的地带长期被思想
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排除在外。
在康有为时代渐行渐远的今日,借助对《意大利游记》的“个案研
究”,重访康氏的思想世界,让我们获益良多。这个“个案”承载着中国
异域志传统,康氏在其中对所经之“国”的山川草木、民情风俗、物质生
· 5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