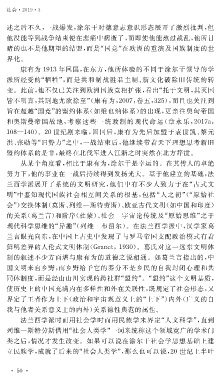Page 57 - 201903
P. 57
社会· 2019 · 3
述之后不久,一战爆发,涂尔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批判,但
他没能等到战争结束便在悲痛中病逝了,而即使他能熬过战乱,他所目
睹的也不是他期望的结盟,而是“国竞”在欧洲的重演及国族制度的世
界化。
康有为 1913 年回国,在东方,他所体验的不同于涂尔干领导的学
派所经受的“牺牲”,而是共和制战胜君主制、新文化破除旧传统的转
变。此前,他不仅已关注到欧洲国族竞相扩张,看出“托于文明,其灭国
皆不明言,其割地尤欲徐至”(康有为, 2007 :卷五, 325 ),而且也关注到
旨在超越“国竞”的盟约体系(如维也纳体系)的出现,更亲往奥匈帝国
和奥斯曼帝国 故 地,考 察 这 些 一 统 政 制 的 现 代 命 运 (章 永 乐, 2017犪 :
108 — 140 )。 20 世纪刚来临,回国后,康有为先后加盟于袁世凯、黎元
洪、张勋等“旧势力”之中,一战结束后,他继续带着天下理想思考新旧
盟约体系的是非,最终在北伐军进入江浙之时突然在北方辞世。
从某个角度看,相比于康有为,涂尔干是幸运的。在其传人的卓绝
努力下,他的事业在一战后持续得到发扬光大。基于他建立的基础,法
兰西学派展开了系统的文明研究,他们中有不少人致力于在“古式文
明”中鉴知现代国族社会相互间关系的根基,包括“人之初”(“原始社
会”)交换体制(莫斯、列维—斯特劳斯)、欧亚古代文明(如中国和印度)
的关系(葛兰言)和阶序(杜蒙)、社会—宇宙论传统及“原始思维”之于
现代科学思维的“异趣”(列维—布留尔)。在法兰西学派中,汉学家葛
兰言眼光向东,在中国上古史中发现了与罗马帝国支配政治模式有着
鲜明差异的人伦式文明体制( 犌狉犪狀犲狋 , 1930 )。葛氏对这一远东文明体
制的叙述不少方面堪与康有为的道德之说相通。如葛兰言指出的,中
国文明来自乡野,而乡野给予它的养分不是乡民的自我封闭心理和共
同体制度,而是经由山川实现的跨社群“盟约”。“盟约”这个文明基质,
使历史上的中国充满内在多样性和外在关联性,既规定了社会形态,又
界定了王者作为上下(政治和宇宙观意义上的“上下”)内外(广义的自
我与他者关系意义上的内外)关系德性典范的属性。
法兰西学派时而用社会学时而用民族学来界定“人文科学”,直到
列维—斯特劳斯借用“社会人类学”一词来统称这个领域宽广的学术门
类之后,情况才发生改变。如果可以说在涂尔干社会学思想基础上建
立民族学,成就了后来的“社会人类学”,那么也可以说, 20 世纪上半叶
· 5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