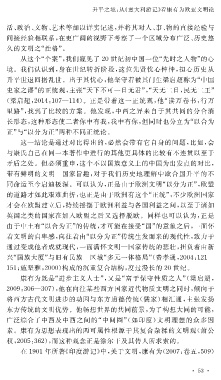Page 60 - 201903
P. 60
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活、政治、文物、艺术等加以详实记述,并将其对人、事、物的直接经验与
间接经验相联系,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考察了一个区域分布广泛、历史悠
久的文明之“性格”。
从这个“个案”,我们窥见了 20 世纪初中国一位“先时之人物”的心
境。我们认识到,身在世纪转折阶段,这位先贤忧心忡忡,担心历史从
升平世退回据乱世。出于其忧心,他坚守着被其门生梁启超称为“中国
史家之谬”的正统观,主张“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 梁启超, 2014 : 107 — 114 )。正是带着这一正统观,他“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找到了比较的方案。他发现,中西之异来自于其共同的分合消
长形态,这种形态使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同时也分立为“以合为
正”与“以分为正”两种不同正统论。
这一结论是通过对比得出的,必然会带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会
与康氏自己在同一本著作中进行的其他更具体的比较有不连贯以至于
矛盾之处。但必须重申,这个不以国族意义上的中国为出发点的对比,
带有鲜明的文明—国家旨趣,对于我们历史地理解中欧合国升平的不
同命运至今启迪极深。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欧洲文明“以分为正”,欧盟
的道路才如此艰难曲折,也正是由于欧洲有这个“正统”,不少欧洲国家
才会在欧盟建立后,持续摇摆于欧洲利益与各国利益之间,以至于诸如
英国之类的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后又选择脱欧。同样也可以认为,正是
由于中土有“以合为正”的传统,才可能在接受“国”的意象之后,一面怀
着文明的自卑感,向往着由“以分为正”传统生发而来的现代性,致力于
通过变成他者成就现代,一面满怀文明—国家传统的悲壮,担负着由新
兴“国族大厦”与旧有民族—区域“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 2004 : 121 —
151 ;施坚雅, 2000 )构成的沉重复合结构,度过漫长的 20 世纪。
康有为既是“进步主义人士”,又是“富于保守性质之人”(梁启超,
2009 : 306 — 307 ),他在向往某些西方国家近代物质文明之同时,倾向于
将西方古代文明进步的动因与东方道德传统(儒家)相汇通,主张发扬
东方传统的文明优势。他畅想世界的共同前景,为了构想大同的可能,
广泛综合了中西及中西之间的“中间圈”(如印度)文明理想的众多因
素。康有为思想表现出的两可属性根源于其复合杂糅的文明观(萧公
权, 2005 : 362 ),而这种观念正是涂尔干及其传人所求索的。
在 1901 年所著《印度游记》中,关于文明,康有为( 2007 :卷五, 509 )
· 5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