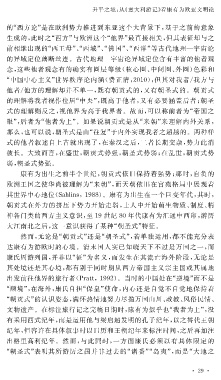Page 36 - 201903
P. 36
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的“西方论”是在欧洲势力推进到东亚这个大背景下,基于之前的意象
生成的,此时之“西方”与欧洲这个“他界”最直接相关,但其表征却与之
前相继出现的“西王母”、“西域”、“佛国”、“西洋”等古代地理—宇宙论
的异域定位藕断丝连。古代地理—宇宙论异域定位含有丰富的他者观
念,这些他者观念有的确实有圈层等级(核心圈、中间圈、外圈)色彩和
“中国中心主义”世界秩序论内涵(费正清, 2010 ),但其对我者/我方与
他者 /他方的理解却并不单一,既有朝贡式的,又有朝圣式的。朝贡式
的理解将我者视作位居“中央”,既高于他者,又有必要涵盖后者;朝圣
式的理解则反之,视他界为高于我界者。故而,可以称前者为“帝国之
眼”,后者为“他者为上”。如果说朝贡式是从“来朝”来理解内外关系,
那么,也可以说,朝圣式是由“往复”于内外实现我者之超越的。两种样
式的他者叙述自上古就出现了,在秦汉之后,二者长期交杂,势力此消
彼长。大致而言,在盛世,朝贡式势强,朝圣式势弱;在乱世,朝贡式势
弱,朝圣式势强。
康有为出生之前半个世纪,朝贡式依旧保持着强势;那时,自负的
欧洲王国之使华尚被理解为“来朝”,而天朝依旧在宫苑格局中展现着
其世界中心地位( 犛犪犺犾犻狀狊 , 1988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巨变年代,其时,
朝贡式在外力的挤压下势力开始走弱,士人中开始萌生物质、制度、精
神各门类的西方主义意识,至 19 世纪 80 年代康有为汇通中西印,游历
大江南北之后,这一意识获得了某种“朝圣式”特征。
然而,无论是“朝贡式”还是“朝圣式”,若单独运用,都不能充分表
达康有为游欧时的心境。清末国人实已知晓天下不过是万国之一,而
康氏周游列国,并非以“征”为名义,而发生在其流亡海外阶段,无论是
其处境还是其心境,都有别于同时期从西方帝国主义宗主国或其属地
出发前往他界的旅行者( 犘狉犪狋狋 , 1992 )。当时的中国处在“逆境”而不是
“顺境”,在海外,康氏自担“保皇”使命,内心还是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
“朝贡式”的认识姿态,满怀热情地努力尽揽万国山川、政教、风俗民情、
文物遗产。在标注旅行记之完稿日期时,康有为似乎也“我者为上”,没
有采用西式纪年,而是运用他与梁启超发明的孔子纪年,以之替代王朝
纪年,但容许在具体叙事时以旧历和王朝纪年来标注时间,之后再加注
出格里高利纪年。然而,与此同时,一方面康氏必须以有具体限定的
“朝圣式”表明其所游历之国并非过去的“诸番”“岛夷”,而是“大地之
· 2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