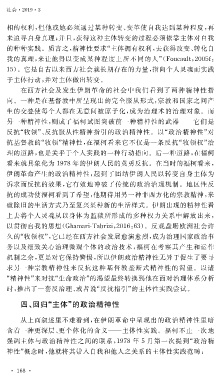Page 175 - 201903
P. 175
社会· 2019 · 3
相的权利,但他或她必须通过某种转变、变革使自我达到某种程度,再
来追寻自身真理;并且,获得这种主体转变的过程必须依靠主体对自我
的种种实践。质言之,精神性要求“主体拥有权利,去获得改变、转化自
我的真理,来让他得以变成某种程度上所不同的人”(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2005犳 :
15 )。它是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长期存在的力量,指向个人灵魂而实践
于主体行动,并对主体做出转变。
在西方社会及发生伊朗革命的社会中我们看到了两种精神性指
向。一种是在基督教中所呈现出的完全服从形式:宗教和国家之间产
生的交叠使每个人都在无意间被原子化,成为治理术的治理对象。而
另一种精神性,则成了福柯试图突破前一种精神性的武器———它们是
反抗“牧领”、反抗服从性精神指引的政治精神性。以“政治精神性”对
抗基督教的“牧领”精神性,在福柯看来它不仅是一条反抗“牧领权”治
理的道路,也是关乎于个人实践的一种行动指向。后一种道路,在福柯
看来就具象化为 1978 年的伊朗人民的英勇反抗。在当时的福柯看来,
伊朗革命产生的政治精神性,起到了团结伊朗人民以转变自身主体为
诉求而反抗的效果,它有效地冲破了传统的政治治理机制。地区性反
抗的成功使福柯看到了希望,他期待用另一种非西方化的宗教精神,来
破除旧的生活方式乃至复兴某种新的生活样式。伊朗出现的精神性看
上去将个人灵魂从以身体为监狱所形成的多种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
以贯彻自我的思想( 犌犺犪犿犪狉犻犜犪犫狉犻狕犻 , 2016 : 63 )。反观盘踞欧洲社会许
久的“牧领权”,它已经在西方社会发展愈演愈烈,成为治理国家政治事
务以及细致关心治理微观个体的政治技术,福柯在考察其产生和运作
机制之余,更是对它保持警惕,所以伊朗政治精神性无异于促生了要寻
求另一种宗教精神性来反抗这种基督教垄断式精神性的渴望。以诸
“精神性”来对抗“生命政治”的渴望最终转换到他在面对治理体系分析
时,推出了一套反治理、或者说“反抗指引”的主体性实践尝试。
四、回归“主体”的政治精神性
从上面叙述里不难看到,在伊朗革命中呈现出的政治精神性里暗
含着一种更深层、更个体化的含义———主体性实践。福柯不止一次地
强调主体与政治精神性之间的联系, 1978 年 5 月第一次提到“政治精
神性”概念时,他就将其带入自我和他人之关系的主体性实践范畴:
· 1 6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