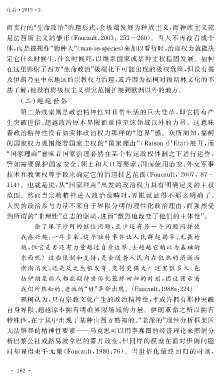Page 169 - 201903
P. 169
社会· 2019 · 3
而实行的“生命政治”治理形式,会极端发展为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就
是法西斯主义的雏形(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2003 : 253-260 )。当人不再被看成个
体,而是被视作“物种人”( 犿犪狀犪狊狊 狆 犲犮犻犲狊 )来加以看待时,治理权力就能决
定它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以维系国家或某种主权稳固发展。福柯
在这里影射了西方“生命政治”极端化下可能出现的极权危险,但没有提
及伊朗乃至中东地区的宗教权力治理,或许因为福柯对穆斯林文化的不
甚了解,他没有将极权主义研究范围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方。
(二)超越世俗
第二条线索则是政治精神性对日常生活的巨大变革,即它拥有产
生突破世俗、超越政治原本界限而延伸至该领域以外的力量。这意味
着政治精神性没有如实体政治权力那样的“边界”感。众所周知,福柯
的国家权力观围绕着国家主权的“国家理由”( 犚犪犻狊狅狀犱 ’ 犈狋犪狋 )展开,而
“国家理由”意味着国家治理必然在某个特定政权体制之下进行运作,
譬如需要保护国家安全、领土和人口等要素,因而使用治安、外交军事
技术和牧领权等手段来确定它的治理技艺范围(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2007 : 87-
114 )。也就是说,从“国家理由”出发的政治权力具有明确定义的主权
范围。然而当宗教精神进入政治范畴时,界限就显得不那么明确了。
人民的政治参与力量不来自于界限分明的理性化政治理由,而强烈受
到所谓的“非理性”意志的驱动,进而“激烈地改变了他们的主体性”:
除了眼下沙阿的继位问题,至少还有另一个问题同样使
我感兴趣:一年多来,这个独特事件让人民群起揭竿、无畏枪
炮,但它是否还有力量越过自身边界、去超越它赖以为基础的
东西呢?这些限制和支持,是会随着人民内在狂热的消退而
渐渐消失,还是反之生根发芽、变得更强大?这里很多人、包
括伊朗某些人都在期待世俗化最终回归的时刻,因这预示着
我们所熟知的、老派的“好”革命出现。(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1988犪 : 224 )
福柯认为,只有宗教文化产生的政治精神性,才或许拥有那种突破
自身界限、超越原本拥有明确界限场域的力量。伊朗革命之所以拥有
特殊性,在于其中出现了某种由西方熟知的、“老派的”理性分析框架所
无法解释的精神性要素———马克思可以用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来照例分
析巴黎公社或路易波拿巴的雾月政变,但同样的模型在面对伊朗问题
时却显得束手无策(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1980 : 76 )。当世俗化最终回归的时刻,
· 1 6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