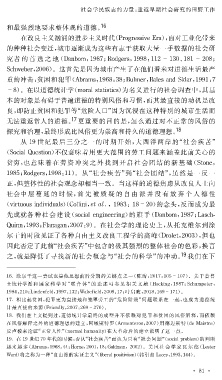Page 88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88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和最强烈地要求整体观的道德。 16
在改良主义汹涌的进步主义时代( 犘狉狅 犵 狉犲狊狊犻狏犲犈狉犪 ),面对工业化带来
的种种社会变迁,城市逐渐成为这些有志于获取大量一手数据的社会研
究者 的 首 选 之 地 ( 犇犪狀犫狅犿 , 1987 ; 犚狅犱 犵 犲狉狊 , 1998 : 112-130 、 181-208 ;
犛犮犺狑犲犫犲狉 , 2006 )。这首先是因为城市产生了在他们看来对道德生活最严
重的冲击:贫困和犯罪( 犃犫狉犪犿狊 , 1968 : 38 ; 犅狌犾犿犲狉 , 犅犪犾犲狊犪狀犱犛犽犾犪狉 , 1991 : 7
-8 )。在以道德统计学( 犿狅狉犪犾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 )为名义进行的社会调查中,其基
本的对象是有碍于普遍道德的特别风俗和习惯,而其最直接的动机是改
良,即防止贫困和犯罪等“危险人口”因为沉浸在这种特别的城市生活而
无法重返常人的道德。 17 更重要的目的是,怎么通过对不正常的风俗的
探究和治理,最终形成比风俗更为崇高和持久的道德理想。 18
从 19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期开始,大西洋两岸的“社会疾苦”
( 犛狅犮犻犪犾犙狌犲狊狋犻狅狀 )不仅意味着用更大范围的劳工问题来涵盖此前关心的
贫穷,也意味着在 劳 资 冲 突 之 外 找到 开启 社会 团结的 新 基础( 犛狋狅狀犲 ,
1985 ; 犚狅犱 犵 犲狉狊 , 1998 : 11 )。从“社会疾苦”到“社会团结”,虽然是一反一
正,但整体性的社会观念却相当一致。当这样的道德焦虑从改良人士向
社会中 层 蔓 延 的 时 候,首 先 被 质 疑 的 自 由 派 并 没 有 放 弃 个 人 德 性
( 狏犻狉狋狌狅狌狊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 )( 犆狅犾犾犻狀犻 , 犲狋犪犾. , 1983 : 18-20 )的念头,反而成为最
先成就各种社会 建 设( 狊狅犮犻犪犾犲狀 犵 犻狀犲犲狉犻狀 犵 )的 旗手( 犇犪狀犫狅犿 , 1987 ; 犔犪狊犮犺
犙狌犻狀狀 , 1993 ; 犉犾犪狀犪 犵 犪狀 , 2007 : 9 )。在社会学的理论史上,从托克维尔到涂
尔干的时段见证了各种自由主义改良工程学的高峰( 犇狉狅犾犲狋 , 2003 ),但也
因此否定了此前“社会疾苦”中包含的极其强烈的整体社会的色彩,换言
之,就是降低了寻找新的社会概念与“社会的科学”的冲动。 19 我们在下
16. 涂尔干这一尝试也是他思想前后分期的关键点之一(陈涛, 2017 : 105-107 )。关于普鲁
士统计学派和 国 家 科 学 对 “联 合 体”的 论 述 可 参 见 相 关 文 献 ( 犎犪犮犽犻狀 犵 , 1987 ; 犛犮犺狌犿 狆 犲狋犲狉 ,
1994 : 210 ; 犔犻狀犱犲狀犳犲犾犱 , 1997 : 132 ; 犠犪犽犲犳犻犲犾犱 , 2009 : 17 ;叶启政, 2018 : 169-171 )。
17. 相比起贫困,犯罪更为直接地和笼罩劳工的“危险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也成为道德统
计最直接的来源( 犉狉犻犲狀犱犾 狔 , 2007 : 269-270 )。
18. 我们在上文提到过,道德统计学最终的成型并不依赖对犯罪和贫困的风俗解释,而依赖
在风俗解释之外的道德理想的建立,阿敏斯特罗( 犃狉犿犲狀狋犲狉狅狊 , 2007 )用德迈斯特( 犱犲犕犪犻狊狋狉犲 )
反卢梭来论证“正常人性”( 狀狅狉犿犪犾犺狌犿犪狀犻狋 狔 )在大革命后的建立说明了这一点。
19. 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否认“社会疾苦”而认为只有“社会问题”( 狊狅犮犻犪犾 狆 狉狅犫犾犲犿 )的判断
越来 越 多( 犃犫狉犪犿狊 , 1968 : 44 ; 犎狅狉狀犲 , 2001 : 18 ; 犌狅犾犱犿犪狀 , 2002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瓦 尔 德 ( 犔犲狊狋犲狉
犠犪狉犱 )将之称为一种“自由派的实证主义”( 犾犻犫犲狉犪犾 狆 狅狊犻狋犻狏犻狊犿 )(转引自 犔犪犮犲 狔 , 1993 : 144 )。
· 8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