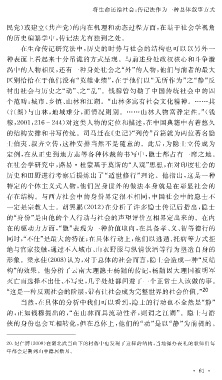Page 68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68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民党)或建立(共产党)的内在机理和动态过程方面,在基于社会学视角
的历史编纂学中,传记法尤有独到之处。
在生命传记研究法中,历史的时势与社会的结构也可以以另外一
种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吊诡的方式呈现。与前述身处政权核心和斗争漩
涡中的人物相反,还有一种身处社会之“外”的人物,他们与前者的最大
区别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英雄业绩”,在于他们以“无所作为”之“静”反
衬出社会与历史之“动”、之“乱”。钱穆曾勾勒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四
个范畴:城市、乡镇、山林和江湖。“山林多寓有社会文化精神。……其
(江湖)与山林,地域难分,而情况则别。……山林人物富静定性。”(钱
穆, 2001 : 216-244 )对这类人物的定位和描述,在中国典籍中有着悠久
的结构安排和书写传统。司马迁在《史记》“列传”首篇就为两位著名隐
士伯夷、叔齐立传,这种安排当然不是随意的。此后,为隐士立传成为
定例,在从正史到地方志等各种体裁的书写中,隐士都占有一席之地。
在社会学研究中,路易·杜蒙基于莫斯的“人观”思想,在对印度社会的
历史和田野进行考察后提炼出了“遁世修行”理论。他指出,这是一种
特定的个体主义式人物,他们置身世外的做法本身就是在彰显社会的
存在结构。与西方社会中的身份界定很不相同,中国社会中的隐士不
一定是宗教人士。胡翼鹏( 2012 )在分析了许多隐士传记后指出,隐士
的“身份”是由他的个人行动与社会的声望评价互相界定出来的。在内
在的驱动力方面,“隐”表现为一种价值取向,在具备孝、义、智等德行的
同时,“不仕”是最大的特征;在具体行动上,他们以逃遁、托病等方式拒
绝与官家接触,通过不入城市、山衣野服与纵情饮酒等行为塑造自身的
形象。梁永佳( 2008 )认为,对于总体的社会而言,隐士会造成一种“反结
构”的效果。他分析了云南大理隐士杨黼的传记,杨黼因大理国被明军
灭亡而选择不出仕、不写史,几乎处处都回避了一个正常士人该做的事。
“这是一种反观社会的阶层,带有让社会成为完整世界的社会价值。” 20
当然,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隐士的行动也不全然是“静”
的,正如钱穆提出的,“在山林而具流动性者,则谓之江湖”。隐士与游
侠的身份也会互相转化,但在总体上,他们的“动”是以“静”为前提的。
20. 纪仁博( 2009 )在湖北武当山下的村落中也发现了这样的结构,当地操办丧礼的歌师们每
年都会定期到山中隐居数月。
· 6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