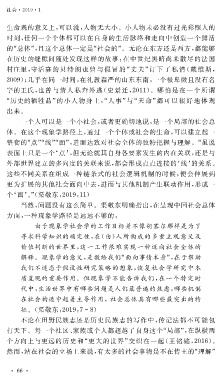Page 73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73
社会· 2019 · 1
生命观的意义上,可以说,人物无大小。小人物未必没有过光彩照人的
时刻,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在自身的生活脉络和走向中创造一个鲜活
的“总体”,且这个总体一定是“社会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能够
在历史的缝隙间随处发现这样的故事:在中世纪黑暗尚未散尽的法国
村庄里,守活寡的 贝 特 朗 也 曾与 假冒 的“丈 夫”订下了 私情(戴 维斯,
2009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礼教森严的山东东南,一个极卑微且没有名
字的王氏,也曾与情人私奔外逃(史景迁, 2011 )。哪怕是在一个所谓
“历史的牺牲品”的小人物身上,“人事”与 “天 命”都可 以很好地体 现
出来。
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小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局部的社会总
体。在这个现象学路径上,通过一个个体或社会的生命,可以建立起一
整套的“点”“线”“面”,进而达致对社会全体的独特把握与理解。“虽说
表面上只是一个‘点’,但无论就其自身各要素发生的内在关联,还是与
外部世界建立的多向度的关联来说,都会形成点点连接的‘线’的关系。
这些不同关系在组成一种链条式的社会逻辑机制的时候,便会伸展到
更为扩展的其他社会面向中去,进而与其他机制产生联动作用,形成一
个‘面’。”(渠敬东: 2019 : 11 )
当然,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渠敬东明确指出,在呈现中国社会总体
方面,一种现象学路径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现象学社会学的工作目标并不像胡塞尔那样是为了
寻求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在(由)人所构成的多重主观意义及
价值判断的世界里,这一工作很难实现一种迈向社会全体的
解释。现象学的意义,是教给我们“面向事情本身”,在于帮助
我们不迷恋于假设性研究策略的想象,恢复社会学研究中本
质直观的重要作用。但现象学不能告诉我们,在一个特定时
代中,生活世界中有哪些问题是人们最普遍的焦虑,哪些机制
在社会构造中起着主导作用,社会总体具有哪些最突出的特
征。(渠敬东: 2019 : 7-8 )
不论在田野民族志还是历史民族志的写作中,传记法都不可能包
打天下。每一个社区、家族或个人都超越了自身这个“局部”,在纵横两
个方向上与更远的历史和“更大的世界”交织在一起(王铭铭, 2016 )。
然而,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来说,有太多的社会事物是不在传主的“理解”
· 6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