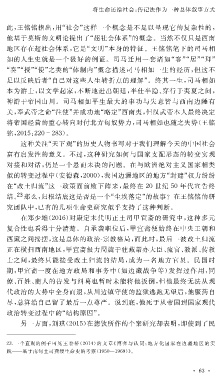Page 70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70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此,王铭铭指出,用“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是不足以呈现它的复杂性的,
他基于莫斯的文明论提出了“超社会体系”的概念。当然不仅只是西南
地区存在超社会体系,它是“文明”本身的特征。王铭铭笔下的司马相
如的人生史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司马迁用一套诸如“客”“居”“拜”
“ 奏”“授”“使”之类的“体制内”概念描述司马相如一生的经历,但这不
足以反映后者“自己对这些人生转折点的理解”。终其一生,司马相如
本为游士,以文学起家,不断地进出朝廷,半仕半隐、穿行于夷夏之间,
神游于帝国山川。司马相如平生最大的事功与失意皆与西南边陲有
关,奉武帝之命“往使”并成功地“略定”西南夷,但汉武帝本人最终决定
将帝国经营的重心转向对付北方匈奴势力,司马相如也随之失势(王铭
铭, 2015 : 220-283 )。
这种关注“天下观”的历史人物书写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
富有启发性的意义。不过,这种研究如何与国家支配形态的转变实现
对接和对话,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与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相类
似的转变过程中(安德森, 2000 ),我国边疆地区的地方“封建”权力纷纷
在“改土归流”这一政策面前败下阵来,最终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宣告终
结。 23 那么,归根结底这是否是一个“尘埃落定”的故事?在王铭铭的研
究团队中,已有的几项生命史研究似乎支持了这种判断。
在郑少雄( 2016 )对康定末代明正土司甲宜斋的研究中,这种多元
复合性也看得十分清楚。自承袭职位后,甲宜斋便始终在中央王朝和
西藏之间摇摆,这是总体的政治 宗教格局,而此时,最后一波改土归流
正在横扫西南地区,甲宜斋极力周旋于驻藏帮办大臣、流官、教派、传教
士之间,最终只能接受改土归流的结局,成为一名地方官员。民国时
期,甲宜斋一度在地方政局和事务中(如边藏战争等)发挥过作用,同
僚、百姓、商人的告发与纠葛也暂时未能将他扳倒,但他最终无法从现
代政治的大势中全身而退,从川边镇守使的监狱逃跑无望后,他服药自
尽,总算给自己留了最后一点尊严。说到底,他死于从帝国到国家现代
政治转变过程中的“结构原因”。
另一方面,刘琪( 2015 )在德钦所作的个案研究却表明,即使到了民
23. 一个直观的例子 可 见 王 春 桥( 2014 )的 文 章 《博 弈 与 认 同:地 方 化 国 家 在 边 疆 地 区 的 实
践———基于南甸土司龚绶生命史的考察( 1950 — 1969 )》。
· 6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