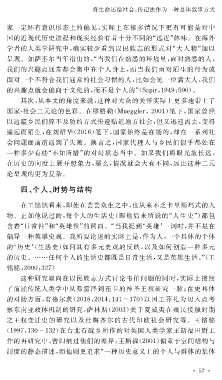Page 64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64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家一定怀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更有可能是对中
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和现实经验有着十分不同的“远近”体味。在海外
学者的人类学研究中,确实较少看到以民族志的形式对“大人物”加以
呈现。如萨丕尔当年指出的,“当我们在熟悉的环境里,面对熟悉的人,
我们的兴趣点通常都会集中在个人身上,而当我们面对陌生的行为或
面对一个不符合我们通常的社会习惯的人,比如会见一位满大人,我们
的兴趣点就会偏向于文化的,而不是个人的”( 犛犪 狆 犻狉 , 1949 : 590 )。
其次,从本文的角度来说,这种对大众的关怀实际上更多地带上了
国家 社会二元论的色彩。在缪格勒( 犕狌犲 犵犵 犾犲狉 , 2001 )笔下,国家曾经
以边疆乡民们猝不及防的方式快速贴近地方社会,但又迅速离去,变得
遥远而陌生;在刘绍华( 2016 )笔下,国家始终是在场的,却在一系列社
会问题面前遭遇到了失败。换言之,国家代理人与乡民们似乎都处在
一种多少有些“不知所措”的对峙状态当中。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
在历史的向度上展开想象力,那么,情况就会大有不同,远比这种二元
论呈现的更为复杂。
四、个人、时势与结构
在王铭铭看来,即使在芸芸众生之中,也从来不乏卡里斯玛式的人
物。正如他说过的,每个人的生活史(即他后来所说的“人生史”)都包
含着“日常性”和“英雄性”的两面。“当我提到‘英雄’一词时,并不是在
倡导一种英雄史观。我所要论述的实际上是,作为人,一个具体的个体
的‘历史’(生活史)如何具有多元史观的反映,以及如何创造一种多元
的历史。……任何个人的生活史都既是日常生活,又是英雄生活。”(王
铭铭, 2000 : 327 )
这种研究取向在以民族志方式讨论韦伯问题的同时,实际上接续
了前述传统人类学中从弗雷泽到霍卡的神圣王权研究一脉;在更具体
的对接方面,有格尔茨( 2018 , 2014 : 141-170 )以国王葬礼为切入点考
察东南亚政体机制的研究,萨林斯( 2003 )关于夏威夷在殖民接触时期
之王权变迁史的研究以及杜梅齐尔的古代印欧社会研究等。王铭铭
( 1997 : 130-132 )在台北石碇乡所作的对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田野工
作的再研究中,曾归纳过他们的差异:王斯福( 2001 )偏重于空间结构与
制度的静态描述,而他则更追求“一种历史意义上的个人与群体的集体
· 5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