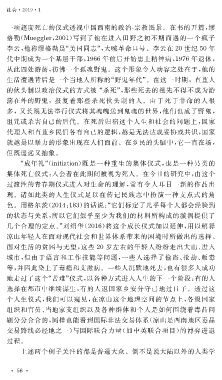Page 63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63
社会· 2019 · 1
一项超度死亡的仪式透视中国西南的政治 宗教图景。在书的开篇,缪
格勒( 犕狌犲 犵犵 犾犲狉 , 2001 )写到了他在进入田野之初不期而遇的一个疯子
李云,他称缪格勒是“美国同志”,大喊革命口号。李云在 20 世纪 50 年
代中期成为一个基层干部, 1966 年前后开始患上精神病, 1976 年退休,
从此四处游荡,彷佛一个孤魂野鬼。这个形象令人动容之处在于,他的
生活遭遇背后是一个当地人所称的“野鬼年代”。在这一时期,直苴人
的伙头制以政治仪式的方式被 “杀死”,那些死去的祖先不得不成为游
荡在外的野鬼,报复着那些杀死伙头制的人。由于死于非命的人很
多,又长期无法举行仪式将其魂魄送到鬼魂的世界,他们也成了野鬼,
诅咒或杀害自己的后代。在死后归宿这个人生和社会的问题上,国家
代理人和直苴乡民们各有自己的逻辑,越是无法达成妥协或共识,国家
就越是以暴力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在乡民的头脑中,它一直在场,
但既遥远又抽象。
“ 成年礼”( 犻狀犻狋犻犪狋犻狅狀 )既是一种重生的集体仪式,也是一种另类的
集体死亡仪式:入会者在此期间被视为死人。在今日的研究中,由这个
过渡性的青春期仪式进入对生命的理解,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出
现。诸如此类的人生仪式足以在传记民族志中扮演一种支点式的角
色。用格尔茨( 2014 : 183 )的话说:“它们标定了几乎每个人都会经验到
的状态与关系,所以它们似乎至少为我们的材料所构成的漩涡提供了
几个合理的定点。”刘绍华( 2016 )将这个成长仪式加以延伸,用以解释
凉山年轻人在面对现代社会和世界体系带来的困境时所做出的选择。
面对生活的贫困与无望,这些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纷纷走出大山、进入
城市,但由于语言和工作技能等问题,一些人选择了偷盗、抢劫、贩毒
等,并因此染上了毒瘾和艾滋病。一些人沉默地死去,也有很多人成功
地走过了这个“苦难”仪式,以各种方式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有的人
选择在都市中继续谋生,有的人返回家乡安分守己地过日子。透过这
个人生仪式,我们可以窥见,在凉山这个地理空间的节点上,各级国家
组织和官员、当地家支组织以及各种群体和个人是如何围绕着毒品问
题分分合合的,同样也能看到国际非法交易体系(凉山是西南地区毒品
交易路线必经地之一)与国际联合力量(如中英联合项目)的博弈进退
过程。
上述两个例子关注的都是普通大众。倒不是说大陆以外的人类学
·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