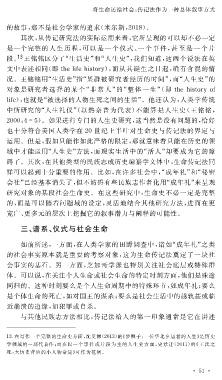Page 58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58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的故事,那不是社会学家的追求(米尔斯, 2018 )。
其次,从传记研究法的实际运用来看,它所呈现的可以却不必一定
是一个完整的 人 生 历 程,可以 是 一 个仪式、一 个事 件,甚 至 是 一 个 片
段。 13 王铭铭区分了“生活史”和“人生史”,我们知道,这两个说法在英
文中表述相同(即 狋犺犲犾犻犳犲犺犻狊狋狅狉 狔 ),而从其诞生之日起,确有含混的情
况。王铭铭用“生活史”指“某群被研究者经历的时间”,而“人生史”的
对象是研究者 选 择 的 某 个“非 常 人”的“整体 一生”(即 狋犺犲犺犻狊狋狅狉 狔狅犳
犾犻犳犲 ),也就是“被选择的人物生死之间的生活”。他还认为,人类学传统
中所研究的“人生礼仪”(以热奈普为代表)不能算是人生史(王铭铭,
2000 : 4-5 )。如果进行专门的人生史研究,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恰好
也十分符合美国人类学在 20 世纪上半叶对生命史与传记法的界定与
运用。但是,假如只能作如此严格的限定,那就意味着只能在历史的领
域中才能运用“人生史”方法,而现实生活中的“活人”却要成为它的障
碍了。其次,在其他类型的民族志或历史编纂学文体中,生命传记法同
样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许多社会中,“成年礼”和“秘密
会社”已经基本消失了,但不妨碍有些民族志作者化用“成年礼”来呈现
研究对象的某段社会生命史。在这些研究中,生命史不必一定是完整
的,而是可以随着问题域的设定,灵活地结合其他研究方法,进而在更
宽广、更多元的层次上挖掘它的叙事潜力与阐释的可能性。
三、谱系、仪式与社会生命
如前所述,一方面,在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中,诸如“成年礼”之类
的社会事实原本就是重要的考察对象,这为生命传记法奠定了一块社
会事实的基石。另一方面,芝加哥学派也特别关注社会底层或特殊群
体。可以说,在关注个人生命或社会生命的特定时刻方面,他们是殊途
同归的。这种时刻要么是个人生命周期中的特殊环节,如成年礼;要么
是个体生命的死亡,如对国王的谋杀;要么是社会生活中的越轨甚或临
近崩溃的边缘,如犯罪或自杀。
与其他民族志方法相比,传记法给人的第一印象通常是它在讲述
13. 在写作一个完整的生命史方面,沈艾娣( 2013 )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是历史
学领域的一部代表作;而在以一个事件或片段为主的人生史方面,史景迁( 2011 )的《王氏之
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可作为范例。
· 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