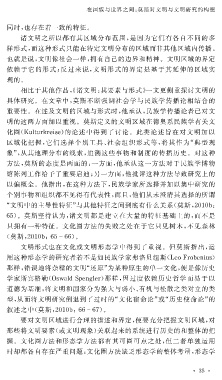Page 42 - 《社会》 2018年第4期
P. 42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同时,也存在着一致的特征。
诸文明之所以都有其区域分布范围,是因为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多
样形式,而这种形式只能在特定文明分布的区域而非其他区域内传播。
也就是说,文明像社会一样,拥有自己的边界和精神。文明区域的界定
依赖于它的形式;反过来说,文明形式的界定是基于其延伸的区域实
现的。
相比于其他作品,《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一文更侧重探讨文明的
具体研究。在文章中,莫斯不断强调社会学与民族学传播论相结合的
重要性。在述及文明的区域与形式时,他承认,民族学传播论者已对文
明的这两方面加以重视。莫斯定义的文明区域在德奥系民族学有关文
化圈( 犓狌犾狋狌狉犽狉犲犻狊犲 )的论述中得到了讨论。此类论述旨在对文明加以
区域化把握,它们选择个别工具、社会组织形式等,将其作为“典型现
象”,从其地理分布的线索,追溯这些事物和制度的传播历史。对这种
方法,莫斯的态度是两面的:一方面,他承认这一方法对于民族学博物
馆陈列工作给予了重要启迪;另一方面,他批评这种方法导致研究上的
以偏概全。他指出,在这种方法下,民族学家所选择并加以集中研究的
个别事物和组织都不见得有代表性,而且,他们从未澄清其选择的所谓
“文明中的主导性特征”与其他特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莫斯, 2010犫 :
65 )。莫斯坚持认为,诸文明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特征基础上的,而不是
只拥有一种特征。文化圈方法的失败之处在于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莫斯, 2010犫 : 65-66 )。
文明形式也在文化或文明形态学中得到了重视。但莫斯指出,运
用这种形态学的研究者若不是如民族学家弗洛贝纽斯( 犔犲狅犉狉狅犫犲狀犻狌狊 )
那样,错误地将杂糅的文明“还原”为某种原生的单一文化,便是像历史
学家斯宾格勒( 犗狊狑犪犾犱犛 狆 犲狀 犵 犾犲狉 )那样,因过度依赖历史哲学而易于以
道德为基准,将文明和国家分为强大与弱小、有机与松散之类对立的类
型,从而将文明研究倒退到了过时的“文化宿命论”或“历史使命论”的
叙述之中(莫斯, 2010犫 : 66-67 )。
要对文明区域进行合理的描述和界定,便要充分把握文明区域,对
那些将文明要素(或文明现象)关联起来的系统进行历史的和整体的把
握。文化圈方法和形态学方法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二者单独运用
时却都各自存在严重问题:文化圈方法缺乏形态学的整体考量,形态学
· 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