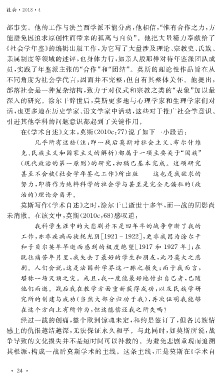Page 31 - 《社会》 2018年第4期
P. 31
社会· 2018 · 4
部事实。他的工作与法兰西学派不能分离,他相信,“惟有合作之力,方
能避免因追求原创性而带来的孤离与自负”。他把大量精力奉献给了
《社会学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它写了大量涉及理论、宗教史、氏族、
亲属制度等领域的述评,也身体力行,如亲人般那样对待年鉴派团队成
员,实践了年鉴派主张的“合作”和“团结”。莫斯的理论性作品旨在从
不同角度为社会学代言,因而并不完整,但自有其整体关怀。他提出,
部落社会是一种复杂结构,致力于对仪式和宗教之类的“表象”加以最
深入的研究。涂尔干辞世后,莫斯更多地与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们对
话,也更多地在历史学家、语文学家中活动,这些对于推广社会学意识、
引进其他学科的问题意识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学术自述》文末,莫斯( 2010犮 : 77 )说了如下一小段话:
几乎所有这些(注:即一战后莫斯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
克、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解析)都属于一项主要关于“国族”
( 现代政治的第一原则)的研究,初稿已基本完成。这项研究
甚至不会被《社会学年鉴之工作》所出版———这也是我欲求的
努力,即将作为纯粹科学的社会学与甚至是完全无偏私的(政
治的)理论分离开。
莫斯写作《学术自述》之时,涂尔干已逝世十多年,而一战的阴影尚
未消散。在该文中,莫斯( 2010犮 : 68 )感叹道:
我科学生涯中的大悲剧并不是四年半的战争中断了我的
工作,亦非疾病而徒耗光阴[ 1921-1922 ],更非我因为涂尔干
和于贝尔英年早逝而感到的极度绝望[ 1917 和 1927 年];在
既往痛苦年月里,我失去了最好的学生和朋友,此乃莫大之悲
剧。人们会说,这是法国科学界这一脉之损失;而于我而言,
堪称一场灭顶之灾。或且,我一度能最好地付出自己者,已随
他们而逝。战后我在教学方面重新获得成功,以及民族学研
究所的创建与成功(当然大部分归功于我),再次证明我能够
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但这能偿还我之所失吗?
经过一战的创痛,整个欧洲惊魂未定,和约是签订了,但各民族情
感上的仇恨越结越深,无法保证永久和平。与此同时,如莫斯所说,战
争导致的文化损失并不是短时间可以补救的。为避免悲剧重现而追溯
其根源,构成一战后莫斯学术的主线。这条主线,正是莫斯在《学术自
· 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