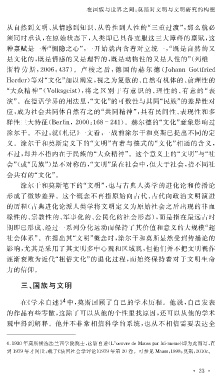Page 30 - 《社会》 2018年第4期
P. 30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从自然到文明、从情感到知识、从兽性到人性的“三重过渡”,那么就必
须同时承认,在原始状态下,人类即已具备克服这三大障碍的禀赋,这
种禀赋是一种“恻隐之心”,一开始就内含着对立统一,“既是自然的又
是文化的,既是情感的又是理智的,既是动物性的又是人性的”(列维—
斯特 劳 斯, 2006 : 437 )。 卢 梭 之 后,德 国 的 赫 尔 德 ( 犑狅犺犪狀狀 犌狅狋狋犳狉犻犲犱
犎犲狉犱犲狉 )等对“文化”加以阐发,视之为复数的、自然有机体的、前理性的
“大众精 神”( 犞狅犾犽狊 犵 犲犻狊狋 ),将 之 区 别 于 有 意 识 的、理 性 的、有 意 的 “表
演”。在德语学界的用法里,“文化”的可数性与其同“民族”的差异性对
应,成为社会共同体自然有之的“共同精神”,具有民间性、表现性和多
样性三大特征( 犅犲狉犾犻狀 , 2000 : 168-241 )。赫尔德的“文化”意象影响过
涂尔干。不过,就《札记》一文看,一战前涂尔干和莫斯已提出不同的定
义。涂尔干和莫斯定义下的“文明”有着与德式的“文化”相通的含义,
不过,却并不指内在于民族的“大众精神”。这个意义上的“文明”与“社
会”(或“民族”)是不对称的,“文明”虽在社会中,但大于社会,指不同社
会共有的“文化”。
涂尔干和莫斯笔下的“文明”,也与古典人类学的进化论和传播论
形成了微妙差异。这个概念不再指原始向古代、古代向政治文明演进
的历程(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将文明定义为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非血
缘性的、宗教性的、军事化的、公民化的社会形态),而是指在最远古时
期即已形成、经过一系列分化运动而保持了其价值和意义的大规模“超
社会体系”。在提出其“文明”概念时,涂尔干和莫斯显然受到传播论的
影响,尤其是采用了其文明多中心观和区域观,但他们并不把文明视作
逐渐衰败为近代“粗俗文化”的退化过程,而始终保持着对于文明生命
力的信仰。
三、国族与文明
在《学术自述》 4 中,莫斯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他说,自己发表
的作品有些零散,这除了可以从他的个性里找原因,还可以从他的学术
观中得到解释。他并不非常相信科学的系统,也从不相信需要表达全
4.1930 年莫斯候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这篇自述( 犔 ’ 狅犲狌狏狉犲犱犲犕犪狌狊狊 狆 犪狉犾狌犻犿犲犿犲 )即为此而写,直
到 1979 年才问世,载于《法国社会学评论》 1979 年第 20 卷。可参见 犕犪狌狊狊 , 1998 ;莫斯, 2010犮 。
·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