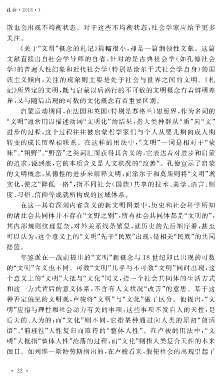Page 29 - 《社会》 2018年第4期
P. 29
社会· 2018 · 4
散也会出现不均衡状态。对于这些不均衡状态,社会学家应给予更多
关注。
《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篇幅很小,却是一篇纲领性文献。这篇
文献直接出自社会学导师的自省,针对的是古典社会学(如孔德社会
学)的普遍人性幻象和近代社会学(特别是涂尔干式社会学自身)的国
族主义倾向,关注的现象则主要是处于社会与世界之间的文明。《札
记》所界定的文明,既与启蒙以后盛行的不可数的文明概念有着鲜明差
异,又与随后出现的可数的文化概念有着重要区别。
启蒙运动期间,在法国和英国(特别是苏格兰)思想界,作为名词的
“文明”通常用以描述动词“文明化”的结果,指人类种群从“质”向“文”
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被启蒙哲学家们与个人从婴儿期向成人期
转变的成长历程相联系。在这样的用法中,“文明”一词是相对于“蒙
昧”、“粗野”、“野蛮”之类词汇而获得其含义的,它表达着对进步和启蒙
的追求,说到底,它的本质含义是人文状况的“改善”。孔德宣示了启蒙
的文明概念,从德性的进步来解释文明,而涂尔干和莫斯则将“文明”现
实化,使之“降低一格”,指不同社会(国族)共享的技术、美学、语言、制
度、习俗、信仰等成就所构成的区域体系。
在这一具有深刻内省含义的新文明图景中,历史和社会科学所知
的诸社会共同体并不存在“文野之别”,所有社会共同体都是“文明的”,
其内部规则纹理复杂,对外关系线条繁复,就历史的先后顺序看,甚至
可以认为,这个意义上的“文明”先于“民族”出现,是相关“民族”的共同
摇篮。
年鉴派在一战前提出的“文明”新概念与 18 世纪即已出现的可数
的“文明”含义也不同。可数“文明”几乎与不可数“文明”同时出现,这
个意义上的“文明”大抵与“文化”同义,指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方式
和这一方式背后的意义体系,不含有人文状况“改善”的意思。基于这
种否定偏见的文明观,卢梭将“文明”与“文化”做了区分。他提出,“文
明”应指与理性和社会动力有关的事项,这些事项不发自人的天性,是
后天的、人为的;而“文化”则不同,它指某种通过向人类的原初“前话
语”、“前理性”天性复归而取得的“整体人性”。在卢梭的用法中,“文
明”大抵指“整体人性”沦落的过程,而“文化”则指人类复合天性的本来
面目。如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在卢梭看来,假使社会的出现引起了
· 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