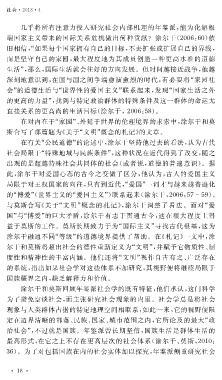Page 25 - 《社会》 2018年第4期
P. 25
社会· 2018 · 4
几乎将所有注意力投入研究社会内部机理的年鉴派,能为化解极
端国家主义带来的国际关系危机做出何种贡献?涂尔干( 2006 : 60 )依
旧相信,“如果每个国家拥有自己的目标,不去扩张或扩展自己的界线,
而是坚守自己的家园,最大程度地为其成员创造一种更高水准的道德
生活”,那么,国际生活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时间越接近战争,他越
深刻地意识到,在国与国之间争端愈演愈烈的时代,有必要将“家园社
会”的道德生活与“世界性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发现“国家生活之外
的更高的力量”,找到与特定政治群体的特殊条件及这一群体的命运无
直接关系的更高尚的生活目标(涂尔干, 2006 : 58 )。
在对内在于“家园”、外延于世界的伦理境界的求索中,涂尔干和莫
斯合写了那篇题为《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的文章。
在有关“公民道德”的论述中,涂尔干坚持他过去的看法,认为古代
社会局限于“特殊地域与民族条件”,这种状况在近代得到了改变,随之
出现的是超越特殊社会共同体的社会(或者说,道德的普遍意识)。据
此,涂尔干对爱国心态的古今之变做了区分,他认为,古人的爱国主义
局限于对王权国家的向往,只有到近代,“爱国”一词才与越来越普遍化
的“博爱”(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涂尔干, 2006 : 57-59 )。
与莫斯合写《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涂尔干调整了看法。面对“爱
国”与“博爱”的巨大矛盾,涂尔干有志于贯通古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莫斯的工作。莫斯长期致力于为“国际主义”寻找古代根基,这为
涂尔干融通不同“等级”的道德境界提供了帮助。在《札记》一文中,涂
尔干和莫斯将超出社会的德性重新定义为“文明”,并赋予它物质性、制
度性和精神性的丰富内涵。他们还将“文明”视作自古有之、广泛存在
的系统,指出如果社会学对这些体系不加研究,其视野便将继续局限于
国族疆界之内,缺乏解释力和价值。
涂尔干和莫斯回顾年鉴派社会学的既有特征,他们承认,这门科学
为了避免空谈社会,而主张研究社会现象的内里。社会学总是将社会
现象与人类群体占据的特定地理空间相联系,如此一来,它的视野便限
定在边界清晰的部落、民族、国家、城市范围之内,它所论及的最大“政
治社会”,不过就是国族。年鉴派曾长期坚信,国族生活是群体生活的
最高形式,在它之上不存在更高层次的社会体系(涂尔干、莫斯, 2010 :
36 )。为了对包括国族在内的社会实体加以探究,年鉴派侧重研究社会
· 1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