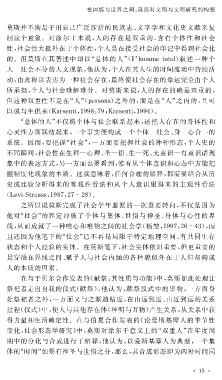Page 22 - 《社会》 2018年第4期
P. 22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莫斯并不满足于用自己广泛涉猎的民族志、文字学和文化史文献来复
制这个意象。对涂尔干来说,人的存在是双重的,含有个体性和社会
性,社会性大抵外在于个体性,个人是在接受社会的印记中得到社会化
的。但莫斯在其著述中却以“总体的人”( 犐 ’ 犺狅犿犿犲狋狅狋犪犾 )叙述一种个
人—社会不分的人文现象,他认为,个人在其人生的时间流动中持续活
动,由此得以表达为一种社会存在,最终使社会存在的命运完全由个人
所承担,个人与社会难解难分。对莫斯来说,人的存在的确是双重的,
但这种双重性不是在“人”( 犲狉狊狅狀狊 )之外的,而是在“人”之内的,且可
狆
以说与生俱来( 犓犪狉狊犲狀狋犻 , 1998 : 79 ; 犓犪狉狊犲狀狋犻 , 1994 )。
“总体的人”不仅将个体与社会联系起来,还把人存在的身体性和
心灵性方面联结起来,一个事实便构成一个个体—社会、身—心合一的
系统。因而,要把握“社会”,一方面要把握社会的种种形态,个人史的
不同瞬间,社会性在生理—心理、圣—俗、生—死、无意识—有意识诸现
象中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惟有从个体意识和心态中方能把
握制度化现象的本质。这就意味着,任何合理的解释,都需要结合从历
史或比较分析得来的客观性看法和从个人意识里得来的主观性看法
( 犔犲狏犻犛狋狉犪狌狊狊 , 1987 : 27-28 )。
之所以说莫斯完成了社会学年鉴派的一次重要转向,不仅是因为
他对“社会”的界定冲破了个体与集体、世俗与神圣、身体与心性的界
线,从而成就了一种唯心和唯物之间的社会学(杨, 1997 : 26-43 ),而
且还因为他笔下的“社会”已不再是局限于特定地理空间、有共同生存
状态和个人经验的实体。在莫斯笔下,社会实体依旧重要,但更重要的
是穿插在界线之间、赋予人与社会内涵的各种貌似外在于人但却构成
人的本质的因素。
在与于贝尔合作发表的《献祭:其性质与功能》中,莫斯如此处理让
祭祀者走出自我的仪式(献祭):他认为,献祭仪式中的事物,一方面身
处祭祀者之外,一方面又与之渐趋贴近,在由远到近、由近到远的关系
过程(仪式)中,使人与其他存在体(神明与万物)产生关系,从关系中获
得力量和生活确定性。在与伯夏合作发表的《论爱斯基摩人的季节性
变化:社会形态学研究》中,莫斯对涂尔干意义上的“双重人”在年度周
期中的分化与合成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以爱斯基摩人为典型,一个集
体的“时间”如果有神圣与世俗之分,那么,其合成形态即为两种时间同
· 1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