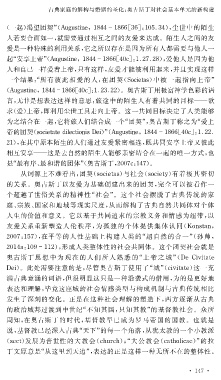Page 154 - 《社会》2018年第3期
P. 154
古典家庭的解构与婚姻的圣化:奥古斯丁对社会基本单元的新构建
(一起)渴望团契”( 犃狌 犵 狌狊狋犻狀犲 , 1844-1866 [ 36 ]: 105.34 ),尘世中的陌生
人若要合而如一,就需要通过相互之间的友爱来达成。陌生人之间的友
爱是一种特殊的利用关系,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所有人都需要与他人一
起“安享上帝”( 犃狌 犵 狌狊狋犻狀犲 , 1844-1866 [ 40犮 ]: 1.27.28 ),爱他人是因为他
人和自己一样爱着上帝,只有这样,友爱才能被利用起来,并且实现这样
一个结果:“所有彼此相爱的人,在团契( 犛狅犮犻犲狋犪狊 )中被一起指向上帝”
( 犃狌 犵 狌狊狋犻狀犲 , 1844-1866 [ 40犮 ]: 1.23.22 )。奥古斯丁用极富神学色彩的语
言,无非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旅途中的陌生人有着共同的目标———欲
求(爱)上帝,即利用尘世工具走向上帝。这一共同目标决定了人类能够
为之结合在一起,它将旅人们结合成一个“团契”,奥古斯丁称之为“爱上
帝的团契( 狊狅犮犻犲狋犪狋犲犱犻犾犲犮狋犻狅狀犻狊犇犲犻 )”( 犃狌 犵 狌狊狋犻狀犲 , 1844-1866 [ 40犮 ]: 1.22.
21 ),在其中原本陌生的人们通过友爱紧密相连,既共同安享上帝又彼此
相互安享———这是去自然的陌生人能够亲密结合在一起的唯一方式,也
是“最有序、最和谐的团体”(奥古斯丁, 2007犮 : 147 )。
从词源上不难看出,团契( 狊狅犮犻犲狋犪狊 )与社会( 狊狅犮犻犲狋 狔 )有着极其密切
的关系。奥古斯丁以友爱为基础创建出来的团契,完全可以被看作一
个超越了世俗关系的精神性“社会”。这个社会摆脱了古典传统的家
庭、宗族、国家和地域等现实尺度,从而解构了古典自然共同体对个体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它以基于共同追求的宗教义务和情感为纽带,以
友爱关系重新塑造人伦秩序,为孤独的个体提供集体认同( 犓狅狀狊狋犪狀 ,
2007 : 157 ),在平等的人性基础上构建人类的“超自然的合一”(孙帅,
2014犪 : 109-112 ),形成人类整体性的社会共同体。这个团契社会就是
奥古斯丁 思 想 中 为 现 在 的 人 们 所 人 熟 悉 的 “上 帝 之 城”( 犇犲犆犻狏犻狋犪狋犲
犇犲犻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奥古斯丁使用了“城”( 犮犻狏犻狋犪狋犲 )这一充
满古典意涵的词语,但很明显这只是一种沿袭式的借用,为的是更好地
表达和理解,毕竟这座城的社会情感类型与构成机制与古典传统相比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种社会理解的塑造下,西方逐渐从古典
的政治城邦过渡到中世纪“不知其国,只知其教”的基督教社会。众所
周知,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基督教早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也就是
说,基督教已经深入古典“天下”的每一个角落,从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
( 狊犲犮狋 )发展为普世性的大教会( 犮犺狌狉犮犺 );“大公教会( 犮犪狋犺狅犾犻犮犪犲 )”的拉
丁文原意是“从这里到天边”,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无所不在的整体性。
· 1 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