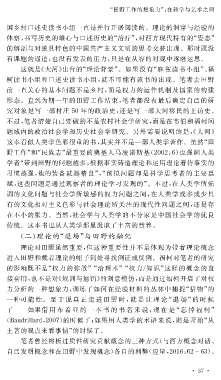Page 44 - 《社会》2018年第1期
P. 44
“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
国乡村口述史读书小组一直是并行开展阅读的。理论的洞穿与经验的
体察,书写历史的雄心与口述历史的“治疗”,对西方现代特有的“姿态”
的解剖与对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思考交替出现。那时既没
有课题的逼迫,也没有发表的压力,只是在从容的对观中琢磨运思。
这就是《大河》出台的“理论背景”。如果没有“麻雀读书小组”、福
柯读书小组和口述史读书小组,就不可能有该书的出现。笔者去田野
前一直关心的基本问题不是乡村,而是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国家的构建
形态。直到为期一年的田野工作结束,笔者都没有最后确定自己的研
究对象是写一部村庄 50 年的政治史,还是写一部大河移民的上访史。
不过,笔者清楚自己要做的不是农村社会学研究,而是在韦伯和福柯问
题域内的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研究。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大河》
这本看似人类学色彩很重的书,其实并不是一部人类学著作。虽然“田
野工作”和“民族志”最重要的奠基人马凌诺斯基( 2002 : 6 )也强调人类
学者“带到田野的问题越多,根据事实铸造理论和运用理论看待事实的
习惯越强,他的装备就越精良”,“预拟问题却是科学思考者的主要禀
赋,这些问题是通过观察者的理论学习发现的”。不过,在人类学所强
调的文化问题与社会学所敏感的权力问题之间,在人类学或多或少具
有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与社会理论所关注的现代性问题之间,还是存
在不小的张力。当然,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不分家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
传统。这本书也从人类学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二)理论的“退场”与田野的融化
理论对田野虽然重要,但这种重要性并不是体现为带着理论概念
进入田野和戴着理论的帽子到处寻找例证或反例。福柯对笔者的研究
的影响既不是“权力的弥散”“治理术”“权力/知识”这样的概念的直
接套用,也不是对《规训与惩罚》的刻意模仿,而是通过福柯开启了对权
力分析的一种想象力,训练了如何在经验材料的丛林中捕捉“猎物”的
一种可 能 性。至 于 说 真 正 走 进 田 野 时,就 是 让 理 论 “退 场”的 时 候
了———如果借 用 布 希 亚 的 一 本 书 的 书 名 来 说,现 在 是 “忘 掉 福 柯”
( 犅犪狌犱狉犻犾犾犪狉犱 , 2007 )的时候了;如果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说,则是开始“从
土著的观点来看事情”的时候了。
笔者曾经辨析过质性研究贡献概念的三种方式(与西方概念对话、
自己发明概念和在田野中发现概念)各自的利弊(应星, 2016 : 62-63 )。
· 3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