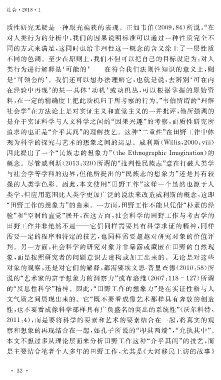Page 39 - 《社会》2018年第1期
P. 39
社会· 2018 · 1
质性研究无疑是一种眼光褊狭的表现。正如韦伯( 2009 : 84 )所说:“在
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中,我们的因果说明标准可以通过一种性质完全不
同的方式来满足,这同时也给非理性这一概念的含义涂上了一层性质
不同的色调。至少在原则上,我们不但可以把自己的目标设定为:对人
类行为进行解释是‘可能的’———在符合我们法则性知识的意义上,则
是‘可领会的’。我们还可以想办法理解它,也就是说,去辨别‘可在内
在经验中再现’的某一具体‘动机’或动机丛,可以根据掌握的原始资
料,在一定的精确度上把此动机归于所考察的行为。”韦伯所谓的“理解
社会学”在方法论上是对实证主义和直觉主义的一并批评,他所强调的
是介于实证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因果兴趣”的考察,而质性研究所
追求的也正是“介乎其间”的理解技艺。这种“二重性”在田野工作中体
现为科学的探究与艺术的想象之间的运思。威利斯( 犠犻犾犾犻狊 , 2000 : 狏犻犻犻 )
因此提出了一个“民族志的想象力”( 狋犺犲犈狋犺狀狅 犵 狉犪 狆 犺犻犮犐犿犪 犵 犻狀犪狋犻狅狀 )的
概念。尽管威利斯( 2013 : 320 )所谓的“批判性民族志”意在打破人类学
与社会学等学科的边界,但他所提出的“民族志的想象力”还是具有较
强的人类学色彩。因此,本文使用“田野工作”这样一个虽然也源于人
类学,但应用范围比人类学更加广泛的说法来改造威利斯的概念,这即
“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由来。一方面,田野工作不能只凭借“朴素的经
验”和“空洞的直觉”展开,在这方面,社会科学的田野工作与考古学的
田野工作并非绝然不通———它们同样需要具有科学求证的精神,同样
需要一定的程序和特定的技艺,也同样需要超越对研究对象的价值评
判。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并非暴露或藏匿在田野的自然现
象,而是按照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去建构或加工出来的。无论是对这些
对象的观察,还是对它们的解释,都需要埃文思 普里查德( 2010 : 58 )所
说的“艺术家的富于想象力的洞察力”或布洛维( 2007 : 118-127 )所谓
的“反思性科学”精神。因此,“田野工作的想象力”是在实证性格与人
文气质之间展现出来的。它“既不要看成像艺术那样具有奔放的创造
性,也不要看成像科学那样具有广负盛名的突出的系统性”(沃尔科特,
2011 : 4 ),而是要将科学的要素和艺术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将真实的观
察和想象的再现结合在一起,如孔子所说的“叩其两端”,“允执其中”。
本文不想过多从理论层面来分析田野工作这种“介乎其间”的技艺,而
是主要结合笔者个人多年的田野工作,尤其是《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 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