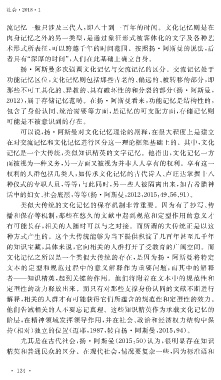Page 131 - 《社会》2018年第1期
P. 131
社会· 2018 · 1
流记忆一般只涉及三代人,即八十到一百年的时间。文化记忆则是在
肉身记忆之外的另一类型,是通过象征形式被客体化的文字及各种艺
术形式所表征,可以跨越千年的时间范围。按照扬·阿斯曼的说法,后
者具有“深厚的时间”,人们在此基础上确立自身。
扬·阿斯曼多次强调文化记忆与交流记忆的区分。交流记忆处于
功能记忆区位,文化记忆则包括那些古老的、偏远的、被转移的部分,即
那些不可工具化的、异教的、具有破坏性的和分裂的部分(扬·阿斯曼,
2012 ),属于存储记忆范畴。在扬·阿斯曼看来,功能记忆是结构性的,
包含了身份认同、统治需要等方面,是记忆的可支配方面,存储记忆则
可能是不被意识到的存在。
可以说,扬·阿斯曼对文化记忆理论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
在对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进行区分这一理论框架基础上的。其中,文化
记忆是一个大传统,类似知识精英的文字记忆。他指出,文化记忆一方
面被视为一种义务,另一方面又被视为并非人人享有的权利。享有这一
权利的人群包括几类人,如传承文化记忆的古代诗人、卢旺达掌握十八
种仪式的专职人员,等等;与此同时,另一些人被隔离出来,如古希腊神
话中的妇女、社会底层,等等(扬·阿斯曼, 2012 , 2015 : 49 、 56 、 91 )。
类似大传统的文化记忆的保存机制非常重要。因为有了抄写、传
播和保存等机制,那些在悠久的文献中起到规范和定型作用的意义才
有可能长存,相关的人随时可以与之对接。而所谓的大传统正是以这
种方式产生的。这个大传统能够为当下提供积淀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
的知识宝藏,具体来说,它向相关的人群打开了受教育的广阔空间。而
文化记忆之所以是一个类似大传统的存在,是因为扬·阿斯曼将特定
文本的定型和规范过程中的意义解释作为重要问题,而其中的解释
者———知识精英,起到关键的作用。他们将附着在文本中的规范性和
定型性的动力释放出来。而只有对那些支撑身份认同的文献不断进行
解释,相关的人群才有可能获得它们所蕴含的规范性和定型性的效力。
他们告诫相关的人不要忘记真理。这些知识精英作为承载文化记忆的
阶层,在精神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中保
持(相对)独立的位置(迈耶, 1987 ,转自扬·阿斯曼, 2015 : 94 )。
尤其是在古代社会,扬·阿斯曼( 2015 : 50 )认为,很明显存在知识
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区分。在现代社会,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标准语和
· 1 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