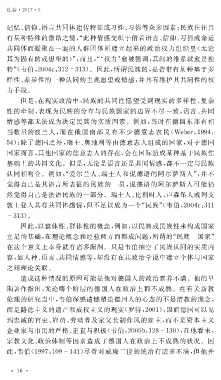Page 23 - 《社会》2017年第5期
P. 23
社会· 2017 · 5
记忆、信仰、语言共同体遗传特征或习性、习俗等众多因素;民族往往具
有某种特殊的激昂之情,“此种情感交织于借着语言、信仰、习俗或命运
共同体而凝聚在一起的人群团体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组织里(无论
其为固有的或想望的)”,而且,“‘权力’愈被强调,其间的维系就愈是独
特”(韦伯, 2004犮 : 312-313 )。因此,所谓民族的,是指带有某种基于多
样性、差异性的一种认同的主观愿望或情感,并具有维护其共同性的权
力手段。
但是,在现实政治中,民族的共同性愿望受到现实的多样性、复杂
性的牵制,表现为民族的分布与民族国家的边界不尽一致,语言、共同
情感等都无法成为决定民族的实质因素。例如,当时在德国东部有相
当数量的波兰人,而 在 俄 国 南 部又有 不少 德意 志农民( 犠犲犫犲狉 , 1994 :
54 );除了德国之外,瑞士、奥地利等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国家,对于德国
国家而言,其他国家的德意志人的存在,会在国际造成某种基于民族性
基础上的共同文化。但是,无论是语言还是共同情感,都不一定与民族
认同相吻合。例如,“爱尔兰人、瑞士人和说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并不
觉得自己是其语言所表征的民族的一员,说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可能仍
然觉得自己是法语民族的一部分。瑞士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或列支
敦士登人具有共同体感情,但不足以成为一个“民族”(韦伯, 2004犮 : 311
-313 )。
因此,以整体性、群体性的概念,例如,以民族或民族性来构成国家
立足的基础,在理论概念和经验两方面都成问题,所谓的“民族—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本身就有诸多漏洞。只是韦伯抽空了民族认同的实质内
容,如人种、语言、共同情感等,却没有在其政治学说中建立个体与国家
之间理论关联。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他对德国人的政治素养不满。他的早
期著作指出,无论哪个阶层的德国人在政治上都不成熟。在有关新教
伦理的研究当中,韦伯深感遗憾塑造德国人的心态的不是清教的理念,
而是路德主义的遗产和威权主义的现实(罗特, 2001 ),因而德国可以见
到忠诚的官吏、雇员、劳动者及家父长制作风的雇主,而不是资本主义
企业家与市民的严格、正直与积极(韦伯, 2005犫 : 128-130 ),在他看来,
宗教文化、政治体制等因素造成了德国人在政治上不成熟的状况。因
此,韦伯( 1997 : 109-141 )尽管对威廉二世的统治有诸多不满,但他并
· 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