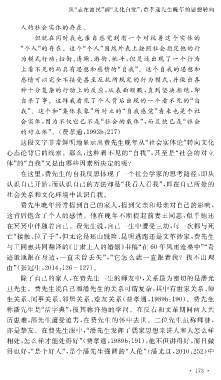Page 180 - 《社会》2017年第4期
P. 180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人的社会实体的存在。
但就在同时我也亲自感觉到有一个对抗着这个实体的
“个人”的存在。这个“个人”固然外表上按照社会指定他的行
为模式行动:扫街、清厕、游街、批斗,但是还出现了一个行为
上看不见的而具有思想和感情的“自我”。这个自我的思想和
感情可以完全不接受甚至反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并做出各
种十分复杂的行动上的反应,从表面顺服,直到坚决拒绝,即
自杀了事。这样我看见了个人背后出现的一个看不见的“自
我”。这个和“集体表象”所对立的“自我感觉”看来也是个社
会实体,因为不仅它已不是“社会的载体”,而且快已是“社会
的对立体”。(费孝通, 1993犫 : 217 )
这段文字非常鲜明地显示出费先生晚年从“社会实体论”转向文化
心态论背后的线索。那么,这种看不见的“自我”,甚至是“社会的对立
体”的“自我”又是由哪些因素所决定的呢?
在这里,费先生的自我反思体现了一个社会学家的思考路径,即从
认识自己开始,而认识自己的方法却是“我看人看我”,即在自己所处的
社会关系和文化环境中认识自我。
费先生晚年经常提到自己的家人,提到父亲和母亲对自己的影响,
这背后饱含了个人的感情。他在晚年不断提起前妻王同惠,似乎她还
在冥冥中伴随着自己。费先生说,自己一生中遭受三劫,每一次都与死
亡“接触、拉了手”,但无论是瑶山脱险、昆明逃跑还是文革抄家,费先生
与王同惠共同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书稿“在 60 年风雨沧桑中”“奇
迹般地跟在身边,一直未曾丢失”,“它怎么就一直跟着我?找不出理
由”(张冠生, 2014 : 126-127 )。
除了自己的家人,在费先生一生的师友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潘光
旦先生。费先生说自己和潘先生的关系可谓复杂,其中有世家关系、师
生关系、同事关系、邻居关系、难友关系(费孝通, 1989犫 : 190 )。费先生
称潘先生是“活字典”,极其称许他的学问。在反右和文革期间两人共
历患难,潘先生遭受迫害,在费先生的怀中去世。二位先生虽称师徒,
亦是挚友。在费先生眼中,“潘先生发挥了儒家思想来讲人和人怎么样
相处,怎么样才能处得好”(费孝通, 1989犫 : 191 ),他不但讲得好,而且做
得也好,“是个好人”,是个潘先生强调的“人伦”(潘光旦, 2010 : 252 )中
· 1 7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