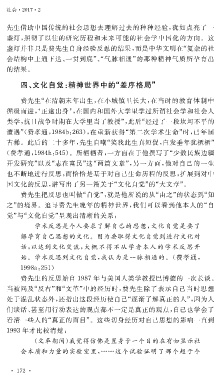Page 179 - 《社会》2017年第4期
P. 179
社会· 2017 · 2
先生借助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去理解过去的种种经验,犹如点亮了一
盏灯,照彻了以往的研究历程和未来可能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这
盏灯并非只是费先生自身经验反思的结果,而是中华文明在“复杂的社
会结构中上通下达、一贯到底”、“气脉相通”的那种精神气质所孕育出
的结果。
四、文化自觉:精神世界中的“差序格局”
费先生“在清朝末年出生,在小城镇里长大,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
循级而进,‘正途出身’,在国内和国外大学里学过所谓社会学和社会人
类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学里当了教授”,此后“经过了一段坎坷不平的
遭遇”(费孝通, 1984犫 : 263 ),在重新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时,已年届
古稀。此后的二十多年,先生自嘲“笑我此生真短促,白发垂年犹栖栖”
(费孝通, 1984犺 : 545 )。所栖栖者,一方面在于他撰写了“少数民族边疆
开发研究”以及“志在富民”这“两篇文章”,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一生
也不断地进行反思,而恰恰是基于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反思,扩展到对中
国文化的反思,谱写出了另一篇关于“文化自觉”的“大文章”。
费先生把反思也叫做“自觉”,就是他所说的从“由之”的状态到“知
之”的境界。追寻费先生晚年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他本人的“自
觉”与“文化自觉”呈现出清晰的关系:
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
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因为要取得文化自觉到进行文化对
话,以达到文化交流,大概不得不从学者本人的学术反思开
始。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我认为是一脉相通的。(费孝通,
1998犪 : 251 )
费先生的反思始自 1987 年与美国人类学教授巴博德的一次长谈。
当被问及“反右”和“文革”中的经历时,费先生除了表示自己当时思想
处于混乱状态外,还指出这段经历使自己“逐渐了解真正的人”,因为人
们谈话、甚至用行动表达的观点都不一定是真正的观点,自己也学会了
看清一些人的“真正的面目”。这些切身经历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一直到
1993 年才比较清楚:
(文革期间)我觉得仿佛是置身于一个目的在有如显示社
会本质和力量的实验室里,……这个试验证明了那个超于个
· 1 7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