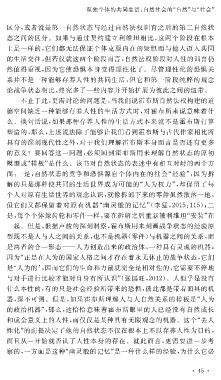Page 52 - 《社会》2016年第6期
P. 52
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区分,或者说是第一自然状态与经过自然法权训育之后的第二自然状
态之间的区分。如果与通过契约建立利维坦相比,这两个阶段在根本
上是一样的,它们都无法保证个体克服内在的疑惧而与他人迈入共同
的生活交往,但若仅就这两个阶段而言,自然法权阶段对人性的训育仍
然值得重视,因为它使恐惧本身变得理性化了。尽管理性化的恐惧关
系并不是一种能够存养人性的共同生活,但它和第一阶段纯粹的观念
论战争状态相比,终究多了一些内容并开始扩展为彼此之间的纽带。
不止于此,更需讨论的问题是,当我们说霍布斯自然法权构建的道
德空间缺乏一种能够存养人性的生活方式时,对霍布斯来说意味着什
么。换句话说,如果那种存养人性的生活方式本来就不是霍布斯打算
塑造的,那么,上述说法除了能够让我们看到霍布斯与古代作家相比所
具有的深刻现代性之外,对于我们理解霍布斯本身而言是否还有更多
的意义?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霍布斯用来理解自然状态的原初
模型或“样板”是什么。该书对自然状态的表述中有相互对峙的两个方
面:一是,自然状态的竞争和恐惧源自个体内在的社会“经验”,因为拆
解的只是那种使共同的生活世界成为可能的“人为权力”,却保留了每
个人对原有生活世界的观念认识,就像拆卸下来的零件虽然散落一地,
但它们又都保留着对原有机器“幽灵般的记忆”(李猛, 2015 : 115 );二
是,每个个体像齿轮和零件一样,要在拆解之后重新被利维坦“安装”在
一起。但是,根据卢梭的深刻洞察,霍布斯用来刻画战争状态的经验原
型既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机器(零件)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而
是两者的合一形态———人为创造出来的政治体,一种具有灵魂的机器;
因为“正是在人为的国家人格之间才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战争状态,它们
是‘人为的’,因而它们的生命和力量就完全是相对性的,它需要不停地
与对手进行比较才能对自身有所认识”(张国旺, 2012 )。人似乎是没有
什么本性的,有的只是社会经验所带来的恐惧,彼此都是带着面具的机
器,深不可测。但是,如果霍布斯理解人与人自然关系的样板是“人为
的政治机器”,那么,这恰恰意味着霍布斯眼里的人已经没有自然成长
和成全意义上的人性,而仅仅是某种具有无限观念的机器。这个“去人
性化”的前提决定了他的自然状态不仅在根本上不以存养人性为目的,
而且从一开始就否认了人性本身的存在。就此而言,更需要进一步考
察的,一方面是这种“幽灵般的记忆”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为什么它必
·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