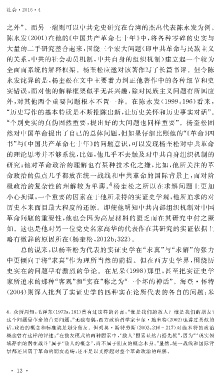Page 19 - 《社会》2016年第4期
P. 19
社会· 2016 · 4
之外”。而另一端则可以中共党史研究在台湾的杰出代表陈永发为例。
陈永发( 2001 )在他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将各种零碎的史实与
大量的二手研究整合起来,围绕三个宏大问题(即中共革命与民族主义
的关系,中共的社会动员机制,中共自身的组织机制)建立起一个较为
全面而系统的解释框架。杨奎松应邀对该著作写了长篇书评。但令陈
永发诧异的是,杨奎松在文中主要着力纠正他著作中的各种细节和史
实错误,而对他的解释框架似乎无甚兴趣,除对民族主义问题有所回应
外,对其他两个重要问题根本不置一辞。在陈永发( 1999 : 196 )看来,
“ 历史写作的基本特质是不断推陈出新,让历史关怀和历史事实对话”。
“个别史实的真伪固然重要,提出好的大问题也同样重要”。杨奎松固
然对中国革命提出了自己的总体问题,但如果仔细比照他的“《革命》四
书”与《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的问题意识,可以发现杨奎松对中共革命
的理论思考并不够系统,比如,他几乎不去触及对中共自身组织机制的
研究;他对革命政治的理解也有某种技术化之嫌,比如,他所关注的革
命政治的焦点几乎都放在统一战线和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上,而对阶
级政治的复杂性的理解较为单薄。 4 杨奎松之所以在求解问题上更加
小心拘谨,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他所秉持的实证史学观,他所追求的对
历史本来面目最大程度的还原。即使他明知中共内部组织机制对中国
革命问题的重要性,他也会因为高层材料的匮乏而在其研究中付之厥
如。这也是他对另一位党史名家高华的代表作在其研究的实证依据上
略有微辞的原因所在(杨奎松, 2012犫 : 322 )。
总的说来,以杨奎松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在“求真”与“求解”的张力
中更倾向于将“求真”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但在西方史学界,围绕历
史实在的问题早有激烈的争论。在尼采( 1998 )那里,甚至把实证史学
家所追求的那种“客观”和“实在”称之为“一个坏的神话”。海登·怀特
( 2004 )则深入批判了实证史学的四种实在论所代表的各自的问题:米
4. 众所周知,毛泽东( 1972犪 : 161 )曾有过这样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无独有偶,西方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 2002 )也讲过类似的
话:政治的概念和标准就是划分敌友。但列奥·斯特劳斯( 2002 : 216-217 )对施米特的政治
概念曾有这样的评述:“在敌友模式的两种因素中,‘敌人’因素显然占据先机”,因为“‘现实领
域存在的潜在战斗’属于‘敌人的概念’,尚不属于朋友的概念本身。”显然,统一战线和国际背
景都还只属于革命的朋友范畴,还不足以支撑起对整个革命政治的理解。
·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