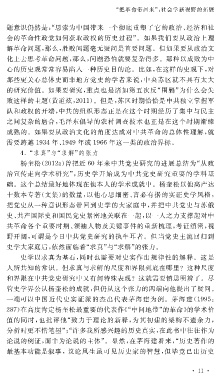Page 18 - 《社会》2016年第4期
P. 18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题意识仍然是:“思索为中国带来一个彻底重塑了它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的革命性政党如何获取政权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要从政治上理
解革命问题,那么,胜败问题毫无疑问是首要问题。但如果要从政治文
化上去思考革命问题,那么,问题恐怕就要复杂得多。那种以成败为中
心的历史观常常容易陷入一种历史目的论。比如,在这样的史观下,对
那些更关心总体史而非地方党史的学者来说,中央苏区就不具有太大
的研究价值。如果要研究,重点也是诸如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
败这样的主题(黄道炫, 2011 )。但是,苏区时期恰恰是中共独立掌握军
队和政权的开端,中共的组织形态正是在这个时期经历了集中与民主
之间复杂的磨合,毛泽东倡导的农村调查技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渐臻
成熟的。如果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达成对中共革命的总体性理解,就
需要跨越 1934 年、 1949 年或 1966 年这一类的政治界标。
4. “求真”与“求解”的张力
杨奎松( 2012犪 )曾把近 60 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总结为“从政
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历史学开始成为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的学科基
础。这个总结最好地体现在他本人的学术成就中。杨奎松以他高产达
十数本专著(文集)的数量,以他心思细密、言必有据的实证史学风格,
把党史从一种意识形态带回到史学的大家庭中,并把中共党史与苏俄
史、共产国际史和国民党史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以一人之力支撑起对中
共革命各个重要时期、领袖人物及关键事件的重新梳理,考证缜密,视
野开阔,可谓是今日中共党史研究的执牛耳者。但当党史主流回归到
史学大家庭后,依然面临着“求真”与“求解”的张力。
史学以求真为基石,同时也需要对史实作出规律性的解释。这是
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求真与求解的尺度和界限到底在哪里?这种尺度
和界限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又有何特殊表现?这就需要慎思明辨了。尽
管史学界公认杨奎松的成就,但仍从这个张力的两端向他提出了疑问。
一端可以中国近代史实证派的杰出代表茅海建为例。茅海建( 1995 :
287 )在高度肯定杨奎松最重要的代表作《“中间地带”的革命》的学术价
值的同时,也批评他“致力于理论的新释,为其初建的架构不遗余力,
分析时更不惜笔墨”;“许多我所感兴趣的历史真实,在此书中往往作为
论说的例证,而非为论说的主体”。显然,在茅海建看来,“历史著作的
最基本功能是叙事,议论风生虽可见历史家的智慧,但毕竟已出历史
·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