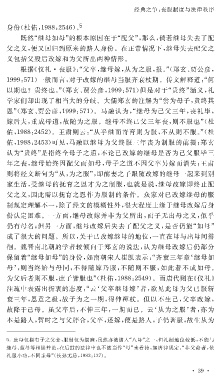Page 46 - 《社会》2016年第2期
P. 46
经典之争:丧服制度与法律秩序
身份(杜佑, 1988 : 2546 )。 5
既然“继母如母”的根本原因在于“配父”,那么,倘若继母失去了配
父之义,便又回归到原来的路人身份。在正常情况下,继母失去配父之
义包括父殁后改嫁和为父所出两种情形。
根据《仪礼·丧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郑玄、贾公彦,
1999 : 571 )一般而言,对于改嫁的继母当服齐衰杖期。传文解释道:“何
以期也?贵终也。”(郑玄、贾公彦, 1999 : 571 )但是对于“贵终”涵义,礼
学家们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分歧。大儒郑玄的注解为“尝为母子,贵终其
恩”(郑玄、贾公彦, 1999 : 571 )。马融认为,“继母为己父三年,丧礼毕,
嫁后夫,重成母道,故随为之服。继母不终己父三年丧,则不服也”(杜
佑, 1988 : 2452 )。王肃则云:“从乎继而寄育则为服,不从则不服。”(杜
佑, 1988 : 2453 )可见,马融以继母为父终服三年丧为制服的前提;郑玄
认为“贵终”是指终全母子之道,不论已改嫁的继母是否为己父服毕三
年之丧,继母始终因配父而如母,母子之道不因父卒另嫁而消失;王肃
则将经文断句为“从,为之服”,即前妻之子跟随改嫁的继母一起来到别
家生活,受继母的抚育之恩才为之制服,也就是说,继母改嫁即终止配
父之义,因此需以抚育之恩作为服制的条件。众家对已改嫁继母的服
制规定理解不一,除了经文的模糊性外,很大程度上缘于继母改嫁后身
份认定困难。一方面,继母改嫁并非为父所出,而子无出母之义,似乎
仍有母名;但另一方面,继母改嫁后失去了配父之义,是否仍能“如母”
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关于已改嫁继母的地位,一直在母与出母间徘
徊。魏晋南北朝的学者较倾向于郑玄的说法,认为继母改嫁后仍部分
保留着“继母如母”的身份,如南朝宋人崔凯表示:“齐衰三年章‘继母如
母’,则当终始与母同,不得随嫁乃服,不随则不服,如此者不成如母。
为父后者则不服,庶子皆服也”(杜佑, 1988 : 2549 )。而唐代则在《仪礼》
注疏中表露出折衷的态度:“云‘父卒继母嫁’者,欲见此母为父已服斩
衰三年,恩意之极,故子为之一期,得伸銺杖。但以不生己,父卒改嫁,
故降于己母。虽父卒后,不伸三年,一期而已。云‘从为之服’者,亦为
本是路人,暂时之与父糞合,父卒,还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从为
5. 庶母仅指有子之父妾,服制仅为缌麻,虽然亦被纳入“八母”之一,但礼制地位较低,不能与
继母、慈母等相提并论,在后世的法律中也不被当作“母”来看待,如唐律规定:“非父命者,依
礼服小功,不同亲母”(长孙无忌, 1983 : 137 )。
· 3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