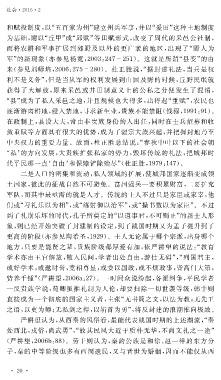Page 27 - 《社会》2016年第2期
P. 27
社会· 2016 · 2
和赋役制度,以“五百家为州”建立州兵军事,并以“爰田”这种土地制度
为基础,附以“丘甲”或“邱赋”等田赋形式,改变了周代的采邑公社制,
而将农耕和军事扩展到郊野及以外的更广袤的地区,出现了“野人为
军”的新现象(亦参见杨宽, 2003 : 247-251 )。这就是所谓“县变”的由
来(参见刘师培, 2006 : 275-280 )。杜正胜说,“据封建礼法,当兵是权
利不是义务”,但是当从军的权利发展到由国及野的时候,丘野民氓就
获得了大解放,原来采邑或井田制意义上的公私之分便发生了混淆,
“ 县”成为了私人采邑之地,并且规模也大得多,出得起“重赋”,农民也
逐渐游离耕地,侵入禁地,寻求新生业,贵族不能禁阻(钱穆, 1991 : 91 )。
在政制上,县设大夫,常由非贵族身份的人出任,同时在士兵招募和收
敛重赋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成为了疆宗大族兴起,并把握封地乃至
中央权力的重要力量。故而,杜正胜总结说:“春秋中叶以下的社会朝
‘私’的方向发展,大贵族扩张私家的势力,毁坏传统的礼法,把城邦时
代平民那一点‘自由’和保障铲除殆尽”(杜正胜, 1979 : 147 )。
二是人口的密集和流动,私人领域的扩展,使城邦国家逐渐变成领
土国家,彼此的征战自然不可避免。富国强兵一要积累财富,二要扩充
军队,而其中最亟需的就是人才。传统的士人不过只是家臣或家宰,他
们或“习礼乐以为相”,或“练射御以治军”,或“操书数以为家臣”。不过
到了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所奠定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新士人形
象,则已经开始突破了封建制的设定,到了战国时期又为孟子提升到了
更高的阶段(亦参见陶希圣, 1929 )。士人无论属于哪个宗派,出身哪个
地方,只要是能贤之辈,贵族阶级都厚爱有加,依严耕望的说法:“教育
学术亦由王官解放,散入民间,学者出处自由,游仕无碍”,“列国君主,
或好学术,或邀时誉,竞相尊显,或委以国政,或不烦政事,皆高门大第,
赀养千锺”(严耕望, 2006犪 : 27 )。一时间众说纷起,各派纠争,平民学者
一反贵族学说,荀卿虽推礼制为人伦,却要扫除一切世袭等级,韩非则
直接成为一个彻底的国家主义者,主张“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
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将反封建的浪潮推向极致。
严耕望认为,从西秦的风俗看,最能代表战国时期的上述潮流,“秦
处西北,戎俗,尚武勇”,“故其民风大近于质朴无华,不尚文礼之一途”
( 严耕望, 2006犫 : 88 )。劳干则认为,秦的公族是和徐、赵一样的东方分
子,秦的中等阶级也多有西周遗民,又与晋世为婚姻,因而不能仅从西
· 2 0 ·